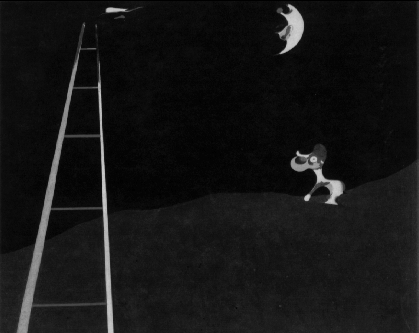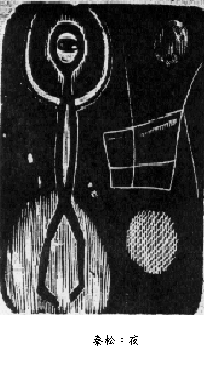超現實的視覺翻譯:
重探台灣現代詩「橫的移植」

版權所有
劉紀蕙
《中外文學》,八十五年24卷8期,第96至125頁
- 談論到台灣文學的現代文學或是現代主義,多數人都會忽略日據時代楊熾昌與林亨泰等人提倡現代文學的努力,而將注意力集中於五○年代創辦現代詩社的紀弦以及當時引起超現實風潮的「橫的移植」之說。本文擬重新探討此現代運動中「橫的移植」的內在模式。
張漢良(1981)曾經為文以超現實主義為例來討論影響研究的問題。張文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為此「超現實主義風潮」公案的編年始末。紀弦在一九五六年《現代詩》13期的宣言中揭櫫其發揚光大自波特萊爾以降包括達達與超現實主義的現代詩派的宗旨,並強調新詩是「橫的移植」,而不是「縱的繼承」。張文指出,《現代詩》「從此以後」譯介多位超現實主義詩人與超現實主義理論,而展開台灣的超現實主義風潮,此風潮至一九六五年亞弦離台赴越南時結束(156)。但張指出,由於我們無法得到足夠的信札、日記、訪談等資料,判斷最具有超現實風格的商禽、亞弦、洛夫等人是透過何種媒介、何項譯作、讀過何人作品而接受影響;同時,張認為,每件作品都是自生的,因此,站在「創作自主的立場上……影響是不存在的」(158)。張的結論是:「影響研究的實證難以確定,影響無法在作品上發現,因此影響研究是沒有意義的」(158);也因此,張自命此文的標題為「影響研究的倣作」,並在文中作了如此的判斷:「一九二○、三○年代的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與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台灣的超現實主義風潮,是中法文學史上,有事實聯繫的類似(parallel),而不斷言他們是文學影響」(149)。
研究比較文學的人都知道,影響研究是傳統比較文學研究的必要法則,尤其是以歐洲研究為中心的法國學派更是認為只有以實證方式進行的影響研究才是合法的比較文學研究。所謂影響研究是指研究不同文化國家的文學,如何因一方(接受者)接觸、翻譯、介紹另一方(發送者)的文學,而影響到接受者本人或其所處文化中的文學現象;而其目的是要藉此建立文學關係史,也就是像是文化交流史一般的多國文學關係網絡史。所謂實證方式是指此類比較文學研究者強調必須有具體可尋的痕跡,如作者的自傳、書信、遊記或訪談中記錄的閱讀經驗,才能開始研究。
張漢良的這篇文章是第一篇以嚴謹的學術討論方式處理台灣的超現實主義風潮的文章,而且他以一貫的清晰思路與批判態度,同時檢視傳統比較文學實證派影響研究的缺失。張漢良指出了傳統影響研究的兩層問題:第一、要談實證的影響溯源,我們似乎有意忽視創作者靈感來源的多樣性與非具體性;第二、我們似乎否定了翻譯作品本身的創作性與文化選擇發展的自主性。
第一個問題「影響來源的多樣性與非具體性」會引導我們面對人類思維的柔軟彈性。一個外國長篇小說中的一句話,或是小說改編成電影時的一個廣告詞或看板畫面,或是友人談話中的轉述,或是畫展中的一幅畫,都可能是不經意的一瞥之下貯存的印象與意象。可能不存在於作者的意識中,或是作者也忘了是何時何地接收到了此訊息。更重要的是,作者自己不會忠實地一一記下他的閱讀材料,他也不會有個左右拾遺,將他的言行記錄下來。如此,要追溯影響源頭可說是緣木求魚,徒然無功。縱使研究者發憤立志,施展地毯式收尋的功夫,整理出一系列接觸關係史的編年表,這對於作家創作的動機、作品內在包涵的問題、外來影響源與本地文化接觸時產生的張力,以及當時本地文化內在錯綜複雜的多重勢力運作,都無法提出適當的詮釋與討論。
第二個問題「翻譯作品本身的創作性與文化選擇發展的自主性」則使我們思考翻譯者在進行文字重寫的過程時,有多少遣詞造句的原則是受到在地文化、文學傳統與當時語言習性所決定?有多少是自己創作意圖導向的字詞鍛鍊?甚至在選擇原作作品時,有多少是基於本地文學要求變革而特意挑選的。此處,我們談到的便是翻譯與接受影響一方的主動性。而每一個翻譯者在著手翻譯時,都免不了隱隱有一些模仿的焦慮與採取諷刺距離的衝動。也就是說,雖然譯者時常不自覺地將翻譯的對象視為一座教堂,而譯者身處聖殿中卻有同時抽身而出嘲弄這位神祗的慾望。當譯者將此原著視為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對象時,他便只是靈媒、乩童,重複原作者的聲音,而無法發揮自己創作的聲音。然而,在譯者企圖脫離原著的控制,而以戲耍的方式玩弄一些出入的伎倆時,創意式的翻譯便發生了,此種翻譯對在地文化的變形影響也隨之產生。
傳統影響研究仍有的第三層問題,卻是張文中未曾提及的,亦即是傳統影響研究受限於「文學研究」中對文字媒體的執著,而忽視了文化運作中多重符號系統互動的問題。這第三個問題「文化運作的多重符號系統互動」更會攤開不同符號系統之間如何互動的討論。文化的構成、轉型與流變,是由多重符號系統交相運作互動所引發。不同文化發生相互滲透的現象時,除了文字的對譯之外,真正發生的亦有視覺經驗的翻譯或是聽覺經驗的翻譯。
也就是說,在文化交流互動時,文學轉譯的不只是文字符號與符碼,亦包含視覺、聽覺或影像的符號與符碼,並利用這些異質文本的意象來豐富文字文本的語彙,或是利用其遵循的異質文法來鬆動文字文本的傳統。
但是,若因為傳統實證影響研究之弊端,而斷言「影響研究沒有意義」,並放棄研究文化交流滲透之種種現象,則是因噎廢食。我們若注意到「影響來源的多樣性與非具體性」、「翻譯作品本身的創作性與文化選擇發展的自主性」,以及「文化運作的多重符號系統互動」的三層考慮方向,便有可能拓展出較為廣義的影響研究。本文便要以文化交流互動時,多重符號系統交織運作的現象,重新檢視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詩壇移植西方超現實風潮的問題。也就是說,本文要以一種廣義的影響研究,打破狹隘的編年史觀點與單一符號系統運作的認知態度,處理包含視覺藝術的間接影響源。本文意圖指出,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文學與畫風皆採保守寫實路數的中國與台灣藝文界中,畫界的李仲生與詩壇的紀弦借用西方的超現實風格,皆是以此文化/藝術「他者」為棧道,暗度當時政治高壓時期被社會潛藏壓抑的革新企圖。而台灣現代詩「橫的移植」超現實詩風,一則是側面借自日本的超現實流派,再則是橫向挪用視覺藝術之超現實構圖,同時也延續了超現實文學與藝術中隱藏的政治抵制。
- 要討論影響的發生,首先便需要回到編年的問題。超現實主義在台灣引發的風潮絕對不是一九五六與一九六五兩個年份能夠界定的。文化轉型的構成因素十分複雜,在台灣文壇五、六十年代宣稱要藉「橫的移植」來促進文學現代化,並有意以文字大量翻譯介紹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宣言與詩作之前, 超現實主義早已藉由日文與視覺藝術的管道橫向輸入台灣文學的不同地層。三十年代由楊熾昌所倡導的風車詩社(le Moulin)所引介的超現實詩風,與三、四十年代的大陸藝壇的現代派移轉到五0年代台灣藝壇的現代派中的超現實畫風,其實是台灣超現實運動的前趨。而且,無論是文字或是視覺藝術,輸入的管道都不是直接銜接法國的文藝界,而是透過日本的文藝界而側面輾轉傳入。
楊熾昌的超現實主義是受到他留日期間在日本盛行的超現實主義與當時大量翻譯為日文的法國超現實主義詩集的影響。二、三十年代正是日本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階段,超現實主義是在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由上田敏雄、上田保、北園克衛等人辦的雜誌《文藝耽美》中被介紹的,該期介紹了阿拉貢(Louis Aragon)、布魯東(André Breton)、艾呂亞(Paul 邮uard)等超現實主義詩人,並刊登了他們詩作的翻譯。一九二七年出版的《馥郁的火夫啊》是日本第一本超現實主義詩集(葉笛 5)。楊熾昌於一九三0年由日本Bon書店以日文出版的《熱帶魚》則是日本自二十年代開始的現代派超現實風潮所影響的結果。一九三五年楊熾昌與林永修、張良典、李張瑞和日本人戶田房子、岸麗子、尚椲鐵平等人於台灣組成的風車詩社是超現實主義在台灣正式結社的行動(葉笛 7)。但是,當時的超現實詩作是以日文寫作發表,而且僅是曇花一現,未能維持太久。不過,由此可得知,當時超現實風格已存在於某些台籍詩人的日文意識層中,而讀者多少也已透過日本本島上的日文詩刊或是台灣島上的日文詩刊接觸到了超現實詩派的風格。
台灣文壇第二次有意識地以文字翻譯介紹超現實主義就是在台灣五、六十年代的現代派運動中發生。《創世紀》、《現代詩》、《笠》等幾種詩刊積極引介歐美現代詩派,尤其是《現代詩》與《創世紀》有意的介紹並練習超現實主義的理論與詩風。 除了歐美的詩作之外,當時這幾種詩刊亦大量譯介日本二、三十年代的超現實主義詩人的作品與翻譯,如佐藤朔、春三、岩佐東一郎等。事實上,我們可以由這些翻譯行為中發現,只有少數詩作是直接從法文或德文翻譯為中文的,多數都是透過日文或是英文的翻譯而轉譯。葉笛於1966年在《笠詩刊》發表布魯東「超現實主義宣言」的節譯,他坦承無法閱讀法文,當時是透過日文的譯本翻譯成中文。 而有意研究並介紹超現實主義理論與詩的洛夫,也說明他無法閱讀德文與法文,都是藉由日文或是英文的翻譯版本來了解超現實主義的(〈我與西洋文學〉 54)。葉笛指出,日本的超現實主義與西方的超現實主義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以主知的力量來建築自我的美學」,並加入東洋的「無」的思維(5)。而洛夫在〈超現實主義與中國現代詩〉一文中強調中國現代詩中的超現實特色主要建立在「對知的熱切要求」以及「禪」的精神(177, 178),這似乎與日本現代派超現實主義的發展有很直接的關連。
除了日本詩壇的影響之外,中國三、四十年代與台灣五十年代視覺藝術的現代化運動也是導致台灣詩壇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之一,但是其過程是扭曲的。因為當時藝壇普遍以寫實保守畫風為主流,而超現實畫風僅是少數藝術家的前衛革命。但是,這少數藝術家的前衛革命,尤其是李仲生,卻刺激了文字工作者如紀弦的前衛革命。
起源自清末民初的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由出國留學接觸到西方繪畫的畫家推動「學習新法」,如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等;而自一九二七年北伐結束,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之間,留學生紛紛返國,帶動現代化普及的盛況 。但是,在討論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旅法藝術家之時,多數藝術史學者皆指出這些畫家無法接受法國當時較屬前衛的畫派。李鑄晉認為這些留學生多半都以比較保守的學院派寫實傳統為學習對象,因此他們回國後亦帶回寫實主義畫風,使其成為中國西畫的主流(李鑄晉 8)。張元茜認為中國早期留法畫家無法接受二十世紀初期流行巴黎的達達、自動主義、即興觀念、現成物體等反藝術潮流的原因是中國畫壇甚至沒有經過文藝復興的階段,因此反藝術對於急於學習西方的中國西畫家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張元茜 46)。就連引發文學界象徵詩派風潮並在詩文中流露超現實風格的李金髮,他的雕塑路線仍然秉持一貫的寫實保守的肖像雕塑(李鑄晉 8;張元茜 46)。
至於同時期台籍留日畫家亦有類似的保守傾向。王秀雄指出,台灣第一代西畫家留日習畫,如顏水龍、廖繼春、郭柏川、李梅樹、李石樵等,所接受的都止於寫實、印象派至野獸派的畫風,而毫無接受當時前衛畫風的痕跡。其中顏水龍、楊三郎與劉啟祥留日後繼續遠赴巴黎學習,留法期間正為一九二0年到一九三五年間超現實主義與抽象繪畫盛行之時,但是他們依舊以留日時的藝術觀點為主,而對巴黎當時的前衛藝術毫無感應(144)。王秀雄指出了一個現象:「台灣籍的第一代畫家,不知是殖民教育使然,總比日本的西畫家來得保守,所吸收的也較狹窄」(143)。其實,這正是被殖民者心態所導致的文化認同與內化。在日本「內地延長」、「皇民化運動」、「國語運動」等文化殖民政策之下,台籍畫家皆以「台展」(1927-1936)與「府展」(1938-1943)反映出的日本內地主流畫風為學習目標,亦以留日習畫為最高的自我要求。日本戰前主導藝壇寫實、泛印象派與野獸派畫風的「文展」是日本畫家成名之管道,人人皆以入選「文展」為志,尤其是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的學生,全年之畫作以文展之主流為習作範圍,也就是所謂「外光派」與「白馬派」的泛印象派。雖然當時日本亦出現具有達達、超現實、抽象派之前衛風格的「二科展」、「春陽會」等在野流派,但是,台灣留日的第一代西畫家,卻自然以日本畫界與學院的主流為認同的目標, 也因此台灣西畫一直以寫實派為主流,頂多夾雜一些泛印象派與野獸派的風格。
在大陸與台灣的畫壇和學院以寫實風氣為主流的保守沈悶環境之下,留日(1933-37)的李仲生引介超現實畫風,創辦現代派大本營的決瀾社,而離開大陸來到台灣後更積極介紹超現實與潛意識等觀念,並促成東方畫會的成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蕭瓊瑞指出李仲生不尋正統學院管道習畫與授課的特色, 或許正是他傾向具有顛覆與革命性格的超現實畫風的原因。李仲生二十歲時與龐薰琴、關良等人組成決瀾社(1930-34),決瀾社的宣言中寫道:
我們厭惡一切舊的形式、舊的色彩、厭惡一切平凡的低級的技巧,我們要用新的技法來表現新時代的精神。
二十世紀以來,歐洲的藝壇實現新興的氣象:野獸群的叫喊,立體派的變形,Dadaism的猛烈,超現實主義的憧憬……。
二十世紀的中國藝壇,也應當出現一種新興的氣象了。
讓我們起來吧!用狂飆一般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來創造我們色、線、形交錯的世界吧!
(《藝術旬刊》1卷5期,1932年十月;引於郎紹君,65。
我們可以看到,在決瀾社呼籲的吶喊聲中,仍然流露出浪漫派「狂飆一般的激情」,這是五四以來尚未發紓盡淨的激情。可見,現代派是當時年輕畫家在保守畫風與社會環境之下,抗拒舊有的傳統、求新求變的方式,尤其是達達的不按牌理出牌與超現實帶來的翻轉現實的視角,對他們來說,都具有絕對的吸引力。留日學生梁錫鴻與李東平等人於一九三五年成立「中華獨立美術協會」,提倡超現實主義藝術,在上海展出抽象畫與超現實畫,同時也展出日本超現實畫家Ai Mitsu 的畫。他們還在十月份的「藝風」專輯刊登布魯東一九二四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並著文介紹超現實主義與其代表性畫家達利(《藝風》一九三五年十月號「超現實主義專號」)(朗紹君 64;Sullivan 104)。一九四五年重慶的「現代繪畫展覽」包括李仲生、林風眠、龐薰琴、關良、趙無極等十三位畫家。其中以李仲生的畫風最為前衛。趙無極日後亦承認,一九四六年重慶的「獨立美展」時,他自己的畫風仍「僅是野獸作風」,而李仲生則為康丁斯基式的抽象繪畫與超現實作風(趙無極 30)。
李仲生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來到台灣時,台灣藝壇仍普遍彌漫保守謹慎的氣氛。李仲生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間在《聯合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新藝術》、《文藝月報》、《技與藝》、《文藝春秋》等刊物發表了許多介紹西方現代畫派的文字,例如《聯合報》一種刊物便前後兩次刊載李仲生介紹超現實主義繪畫的文章(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以及多篇介紹日本前衛畫派的文章(蕭瓊瑞 98-100)。從李仲生本人對超現實主義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出他已脫離法國布魯東等人以自動技法來定義超現實主義的說法。他認為超現實主義把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事物表現在同一畫面上的作法,應該是如德國佛蘭茲•洛(Franz Roh)所謂的「Magischer Realismes」(「魔術的寫實主義」)的說法更為恰當(〈超現實派繪畫〉25)。李仲生認為超現實文學中的自動主義在講究技巧的繪畫中是難以實行的。他認為超現實主義繪畫以「悖乎普通的畫理,而採用了自然悟得的方法。不依靠寫實,而用一種特意的表現,以期暴露人理性的斷面」。因此,由自發主義與偶然性所產生的物與物之間不可思議的對立關係,在繪畫中便成為轉換動與靜、大與小、高下、縱橫等處理,而「排斥那從來的固定底觀念與習慣,或者形式等等的革新性和發展性」便是超現實主義的核心意義了(〈超現實主義繪畫〉 24)。
李仲生選擇放棄超現實主義中的自動技法, 而強調其理性的技法,流露出他企圖顛覆傳統固定觀念與習慣的革命潛力。這在他一九三四年參加日本二科會二十一屆畫展的作品中亦可看出端倪〔見附圖〕。
畫面上,一個由嚴謹透視強制規範的封閉空間與不合透視原則的瓶子造成兩種空間擠壓而產生了突兀的視覺經驗。遠景有輪船的海景暗示一個遙遠而廣闊的天地,前景釘在地面上的紙片上放置的鐮刀與榔頭則強烈暗示文藝革命的必要。但是,在當時政治氣氛緊張的時刻,文藝革命隨時可被套上思想問題的帽子而招致生命危險。與李仲生一起合辦美術班、與台籍文人呂赫若、楊逵、王白淵、雷石榆、周青等人相從甚近的黃容燦便被以匪諜之名逮捕槍決。此事或許是成為李仲生日後緘默的原因之一。
詩人羅門在談李仲生的畫以及其偏向於超現實畫派的畫風時,他的詮釋透露出的卻是他個人向來追求無限的浪漫情調,而忽略了李仲生畫作中隱藏的顛覆革命衝動。羅門指出超現實畫派的特色在於其「溶化一切在潛在意識與經驗中,使思想與精神活動的原型,透過心象,以無形之形,自由自如的呈現於畫面上,產生純然屬於內心無限的追索與看見」(57)。羅門認為,「在李教授的心眼中,任何外在單一或數量性的『形』,都有其可想像得到的極限性,無法成為李教授傳達『心視世界』的最理想的『出口』;最理想的『出口』,是讓『心視世界』,直接以心像的無形之『形』來充當,更能彼此配合,充分發揮:更能達到心態與藝術活動高度自由性與純粹性的效果」(57-58)。雖然羅門也指出了李仲生內在視覺世界在畫布上轉化的自由,但是,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如何以他個人的視角與理想來改寫超現實主義,並且重新定義。
激進的李仲生弟子於一九五六年成立「東方畫會」, 成員如蕭勤、夏陽、吳昊、歐陽文苑、霍剛等人的畫作,更是台灣現代畫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由一九五七年11月東方畫展展出畫家風格的簡介中,我們可看出此次畫展的超現實成分:
金藩: 最初研究立體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後復融入超現實主義之表現法,作風富濃烈稚拙之趣味,並具有一種神秘的幻想和澀的感覺,個性顯著。
夏陽: 最初從事新古典主義的製作,然後受機械主義、表現主義及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和啟示,並同時研究中國的線底結構原理和民間藝術之特質…
歐陽文苑:早期研究立體主義底構造原理,並受齊里柯(Chirico)的造型的象徵主義,及表現主義的影響…
霍剛: 最初為超現實主義研究者,後通過後期立體派的抽象的構成原理,並溶入了潛意識作用,表現著具有濃烈的象徵意味底抽象性底超現實主義繪畫,富有童話般底趣味,個性至為顯著。
蕭勤: …使用自動性技巧而形成一種具有夢幻般底詩意的表現樣式,個性至為明顯,觀其畫如入夢境,富有神秘意味。(蕭瓊瑞《五月與東方》121—122)
一九五六年東方畫會的成立,一九五七年東方畫展的展出,和一九五六年一月現代派詩人集團成立,與洛夫和亞弦在一九五九年先後刊登於《創世紀》的《石室的死亡》與〈深淵〉,都可說是當時整個社會保守高壓氣氛中必須發展出來的文學與藝術的革命。現代詩人紀弦、商禽、辛鬱、楚戈等人都在東方畫展開幕當日到場,紀弦還即興朗誦一首詩(吳昊 81;引於蕭瓊瑞 119)。辛鬱、羅馬、楚戈、秦松、向明等人還每天在畫廊助陣,晚上並在夏陽、吳昊、歐陽文苑等人所借的空總防空洞附設的洞中畫室內飲酒談詩畫(楚戈 10-11;引自蕭瓊瑞 120)。
- 現在回頭檢視台灣五十年代的文學現象,我們發現那時代是處於一種沒有語言與沒有形式的尷尬狀態,前衛詩人與藝術家只能積極的尋找新的語言與文法,而五十年代的現代派則是當時台灣前衛藝術家與文人不得不發展的語言革命。當時那種情況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台籍作家在近一百年之間,幾度面對語言被迫廢棄轉用的困難環境:首先,日本佔據台灣五十年 (1895-1945),台灣人民全面接受日式教育,愈是知識份子,愈被納入日式教育系統之內。其次,由於時代所趨,傳統漢文已不合時宜,二、三十年代作家便嘗試以胡適所倡的白話文寫作,但是,他們缺乏語彙、缺乏形式,所寫出的文字今日看來多半顯得十分生澀幼稚。巫永福〈遺忘語言的鳥〉中清楚描述「遺忘語言的鳥呀/也遺忘了啼鳴/…遙遠的拋棄祖宗…/甚麼也不能歌唱了/被太陽燒焦了舌尖」這種失去語言的困境與悲哀。日據時代後期的皇民化國語運動(1937-1945) ,禁用漢語,更造成台籍作家必須放棄漢文創作。以日文創作的龍瑛宗便犀利地指出台籍作家失去語言的窘境:台灣人「極端拙於口舌,是語彙的貧窮者,…他們的作品,世界觀淺顯,談不上技巧,連必要的言語也找不到」(〈熱帶的椅子〉,引於羅成純 262)。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又於一九四七年開始全面禁用日文,台籍作家再度面臨被迫剝奪語言的處境。同時,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引發的白色恐怖時期,牽連無數,無論是台籍或是外省籍的作家,都面臨了有話不能盡說的政治壓力。傳統語言無法提供當時文藝創作者有效的發紓管道,他們需要用更曲折隱晦的語言,連結表面上無意義的意象,才能使底層的意義一層又一層的轉化。超現實風格正是此管道。
由當時畫壇與詩壇互動的關係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超現實主義的詩與宣言被正式翻譯為中文介紹到台灣詩壇之前,視覺藝術已然先以另一種方式——視覺的方式——展開中國文人的視角。台灣現代派詩人如紀弦、商禽、辛鬱、亞弦、羅馬、楚戈、秦松等人對現代視覺藝術的愛好,可讓我們窺見其詩中視覺意象之構成痕跡。超現實畫作中視覺意象的無理性拼貼提供了詩人心靈一種超現實的層面,當他們以文字重現這種心靈空間的同時,也打破了正統文法規則,而創造出屬於現代詩的一種新的文法。更具體的說,詩人取用屬於畫布上的意象,拼貼於另一現實層面,被取用的意象保留原來的形象符號,但其意含卻被取消。不具有指涉作用的符號拼貼在與原來出處無關的平面上,產生了縱向的意義斷裂,而幾個來自不同現實的中空符號拼貼在詩人的文字平面上,更衝撞出橫向的意義斷裂。
關於現代詩中以視覺經驗翻譯意象而引發現代派的興起,現代派的先驅李金髮可以提供一個有趣的例子。李金髮留法主要的目的是去學習雕塑,而他返國後的正業亦是雕塑,同時,他的雕塑與素描都是以寫實為主,甚至他具代表性的雕塑作品都是當時政壇名人如伍庭芳等人的肖像。李金髮留法期間(1919-1925)在法國盛行的達達與超現實主義,對他的視覺藝術似乎絲毫沒有影響。但是,他在那段時間閱讀的波特萊爾、魏爾蘭、保爾•福爾等象徵詩派的詩作卻成為日後掀起中國現代新詩象徵派熱潮的起源(陳厚誠 71-79)。其實,在仔細閱讀李金髮的詩句後,我們會同意李鑄晉與張元茜所稱李金髮「詩文中流露超現實風格」(李 8;張 46)。例如〈夜之歌〉開頭的幾行:「我們散步在死草上,/悲憤糾纏在膝下。/粉紅色之記憶,/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很明顯的,這是幾種不同現實的意象拼貼於同一層次的文本,而造成意念的拮抗,而鋪陳出如夢魘般的鬼魅氣氛。李金髮在雕塑人像時無從宣洩的悲觀、反體制、幻滅、荒謬與哀傷,卻在他視覺化的文字中流露。
紀弦是以視覺經驗翻譯超現實畫風的另一個重要例子,而他的經驗直接促成了台灣現代詩的發展。紀弦於一九三三年畢業於蘇州美專,一九三六年赴日,返國後從事美術教育,一九四八年來台,在大陸期間已出版過幾部詩集(《紀弦自選集》「小傳」 1)。留日期間,紀弦「直接間接地接觸世界詩壇與新興繪畫,…眼界大開,於是大畫特畫立體派與構成派的油畫,也寫了不少超現實派的詩」(紀弦〈在人生的夏天〉)。他的自畫像很顯然地流露出了達利式的自負狂傲〔見附圖〕。
紀弦自稱受到戴望舒自由詩的音樂性與李金髮「新奇而且古怪」的詩風影響,而開始向「現代」月刊投稿(紀弦〈三十年代的路易士〉)。從他的詩作中我們可清楚看出視覺藝術對他的影響,以及他對西方現代派畫家的熟悉。 例如「夢回」這首詩:
醒來見午夜的月色窗上
剪貼著梧桐樹葉、星和壁虎的
新派圖案。
踩斷初織夢的一線,
歌著幻異下扶梯的貓,
現在和另一匹
開始談起戀愛來了。
詩中拼貼「梧桐樹葉」、「星」、「壁虎」和唱歌的「貓」等毫不相關的意象以及呈現一種夢幻的氣氛,顯然是要呈現超現實畫派的風格。
而紀弦一九四二年的「吠月的犬」則是翻譯超現實繪畫最有意思的例子:
載著吠月的犬的列車滑過去消失了
鐵道嘆一口氣 。
於是騎在多刺的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們的有個性的歌聲四起了:
不一致的意義 ,
非協和之音 。
仙人掌的陰影舒適地躺在原野上 。
原野是一塊浮著的圓板哪 。
跌下去的列車不再從弧形地平線爬上來了 。
但擊打了鍍鎳的月亮的悽厲的犬吠卻又被彈回來 ,
吞噬了少女們的歌 。
奚密在「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當紀弦寫「吠月的犬」時,在大陸發行的《現代》月刊上並沒有超現實詩的翻譯,但卻有介紹包括超現實主義與意象派的現代藝術(5)。奚密之文已隱隱指出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前身應往中國三十年代的現代派追尋,但當時的文壇卻不如當時的藝壇般接觸過超現實主義。而透過習畫背景與留日經驗接觸過超現實藝術的紀弦,借用米羅的畫,發展了一種前衛的文法與意象排列方式。若不看米羅的原畫,紀弦的詩中彼此毫不相干的意象在意義層面上簡直無從銜接。紀弦藉著米羅的畫尋找到了一個大膽陳列意象的藉口。米羅的畫「吠月的犬」〔見附圖〕中的幾個意象也被紀弦有意改寫,重新詮釋其符號,賦予其屬於紀弦個人的意義。 原畫中攀登天空的梯子,被改寫為嘆氣的鐵道,畫中聽不到的犬吠聲,被翻譯成「淒厲的」聲音,「擊打」月亮卻又被「彈回來」,而「吞噬了」少女們「有個性的歌聲」。
我們可以借用Ekphrasis的理論來討論紀弦改寫視覺藝術文本與外來文化文本引發的一些問題。 Ekphrasis 的意思是「使圖像說話」,任何描述視覺藝術的文字都可稱為 Ekphrasis, 我們可以暫時將 Ekphrasis 譯為「讀畫詩」。Murray Krieger (Ekphrasis 1992) 將 "Ekphrastic principle" 定義為描述繪畫或雕塑,使文字呈現繪畫與雕塑的空間感的原則 (9),而他指出"Ekphrastic aspiration" 是一種同時要求凝固與流動的衝動,語言要求將自身凝固為一空間之形,卻又自覺本身無空間性的矛盾而求解脫此形 (10)。而W.J.T. Mitchell 指出, Ekphrasis Image 像是個 「不肯屈服的他者」 ("intransigent Other"),是個文本中的他者(textual Other),是自身的「符號他者」(semiotic Others, 699)。文本要克服這個符號他者。但是,這個符號他者像是個「黑洞」,對抗詩人想要穿透佔有的聲音 (700)。 Ekphrasis Fear 與 Ekphrasis Hope, 根據 Mitchell 的說法,是作者對與「社會他者」結合的畏懼與希求(706);而在文字的再現與視覺的再現之間的符號差距(semiotic gap),便是文本中面對他者的場域(716-717)。 Caws 進一步指出,在一作品中,文字與視覺意像的交集是兩種文本的相互介入、打斷 ("interference," "interruption") ,同時,這種介入會產生內在對話, 透過對話的衝動,牽引出文字文本對視覺文本的慾望以及企圖描述/包涵視覺文本的焦慮。Caws 認為,在「讀畫詩」中,文本透過評論一件藝術品來決定身為讀者與批評家的詩人閱讀此藝術品的角度,而詩人兼批評家的閱讀是一種壓力與焦慮狀態的閱讀 (Caws 8)。
以上述之角度來觀察紀弦對待視覺藝術以及西方超現實主義這兩層內在自我的「黑洞」——「藝術他者」與「文化他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身兼讀者、批評者與詩人的紀弦,在挪用西方藝術形式時,其文字中流露的想要合而為一的慾望與害怕被吞併的焦慮。米羅畫中這些斷裂的意象被紀弦強制拼貼,而造成了紀弦詩中文本表面極端不協調的張力。米羅的視覺文本是紀弦以文字所描述/篡改的對象。而在紀弦式「讀畫詩」的文字改寫圖像的例子中,我們面對兩個文本之間的辯証關係:紀弦的文字迫使自身塑造也同時瓦解米羅的視覺文本之形,而在文字與被解消的視覺文本之間又兼含慾望與焦慮的對話。紀弦將另一種藝術形式與外來文化,在他的文字中轉化為文本中的「符號他者」:一個不在場卻被召喚的黑洞,控制文字的發展。在視覺符號與文字符號的斷裂處,在紀弦以文字改寫米羅的視覺文本而賦予聲音時,我們聽到了詩人的焦慮:詩人企圖揭露卻又畏懼被識破的內在社會他者,一個在政治高壓之下的異端。
「嘆一口氣」的鐵道,「淒厲的」犬吠,少女「有個性的歌聲」,「非協和之音」,對紀弦來說都是十分有意義的。在另一首詩「回聲」中,詩人自擬檳榔樹,並說:
他佇立著,像一棵生了根的檳榔樹。
他凝望著天邊,怪寂寞地。
……
…他已深深地厭倦於
空谷裡太多的回聲
和回聲的回聲,的回聲……
那些沒個性的,多麼可憎。(《紀弦詩選》301)
紀弦一輩子強調「個性」的重要,其詩中亦一再出現對此概念的發揮。對紀弦來說,為政治宣傳的文字是沒有個性的文字。他曾在一九四八年獨資創辦的《異端》詩刊的宣言中稱:「我們主張一切文學、一切藝術的純粹化;特別要把詩從政治中解放出來,使其獨立生存,自由發展。…〔赤色梵蒂崗的桂冠詩人〕抹殺個性;我們崇尚個性」(〈從1937年說起〉 84)。到台灣以後,他也對國民黨抹煞詩人個性的政治文藝路線提出類似批判:「恕我率直地指出來吧,流行在今日之詩壇上的,有一種最要不得的傾向,那就是『意識至上主義』。…凡是宣傳反共抗俄的,都是好的;…這原是共產黨的文藝政策之一要點;…想不到在今日之台灣,竟又抬起頭來,而且耀武揚威」(《紀弦詩論》 38)。在文壇與政治生態中沒有個性、只有回聲的時代裡,少女們有個性的歌聲,「不一致的意義,非協和之音」,是一種變調,一種抵制。但是,在這一塊像是「浮著的圓板」的原野上,不協和而有個性的聲音是不被容許的,連要抗議的吠月之犬也不再存在。而米羅逃離地面、通往天空,童稚趣味十足的梯子, 被紀弦詮釋成供列車通過的鐵軌,列車的進行不容分辨,無法停止。這鐵軌是單向的,載著吠月之犬離開的列車跌落弧形的地平線後便不再爬起來了。仰頭所望到的月亮不是可供思鄉的月亮,而是被「鍍(了)鎳」了月亮,具有金屬性質的堅硬表面,是不能溝通不能接納聲音的意識型態。不被接納的淒厲的犬吠被月亮彈了回來,連僅存的少女有個性的歌聲也被淹沒了。
對紀弦來說,超現實主義是為了配合他自己的理念而選擇接受與挪用的,他策略性地在現代派中凸顯超現實主義,主要是作為他批判左派的浪漫主義與共產黨文藝路線強調的寫實主義的工具。他在〈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一文中說:
要冷靜!要清醒!但同時又不可缺少一種「超現實」的精神。此乃「深入現實」的超現實,而非「游離現實」的超現實,即「現實的最深處」之探險與發掘(161)。
這段話很明顯地是利用超現實主義來對抗浪漫主義,以強調現代精神中的冷靜、清醒與探險最深處現實的精神。紀弦也利用超現實主義反對寫實主義,他先後在《現代詩》的刊頭介紹秦松十分具有超現實風格的版畫,如第十九期的「群像」與「夜」〔見附圖〕,

並特意為文推薦秦松的版畫,而紀弦的推薦文字正顯示出他的詩觀:文中他強調此版畫中的「個性」與「超現實境界」和詩的「不表現凡散文所能表現的,剔除了一切攝影所能作到的」特色相近(十九期刊頭)。可見紀弦所以推崇超現實主義,便是因為他認為所謂超現實主義呈現的是「『企圖現實之最深處』,唯心眼可以看見,而攝影機無法攝下來的現實」(《紀弦詩論》〈論想像〉 54)。紀弦也說:「繪畫是主觀自然的創造,攝影是客觀自然的抄襲。無個性的再現不是藝術,藝術是有個性的表現」,而超現實主義是「使自然變貌,在畫幅上作夢幻的行動」(〈詩是詩、歌是歌、我們不說詩歌〉 11)。
紀弦有選擇性的接受超現實主義,卻不願自稱為是超現實主義者,並激烈反對超現實主義所提倡的自動寫作。他屢次強調:「我們的新現代主義」不是法國的超現實主義的同道,他並且譴責當時詩人群中「有一些人在啃著法國的超現實主義的麵包乾而自以為頗富營養價值」(〈從自由詩的現代化到現代詩的古典化〉 31)。紀弦多次「大聲」否認他是超現實主義者,並強調超現實主義中的「自動的記述」是「現代派所不取」:
在我看來,所謂「潛意識」也者,固然是真實地存在於人類心靈深處的現實之一種,但是完全不受理性控制的「自動文字」則為事實上的不可能。(「多餘的困惑及其他」 96)
紀弦同時指出超現實派所企圖表現的「潛意識」與其所利用的「自動文字」和象徵派受高度理性控制的文字,是相對立的。他並且判定,超現實派的「自動文字」必須被揚棄,而象徵派的音樂主義也是必須被揚棄的(100-101)。可見,紀弦與李仲生一樣,取用超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是其中高度理性控制不同層面現實之反常理拼貼而處理的政治抵制。
紀弦式以文字「翻譯」視覺藝術的例子,在五、六十年代台灣現代詩人的超現實詩作中比比皆是。詩人們以文字再現視覺藝術,化形象為文字,改寫形象符號的指涉符碼,並借用西方超現實畫派拼貼表面上無關連的形象的非理性邏輯為文字的構成文法。例如林亨泰的「軟管擠出的春天」,洛夫的「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石室之死亡》 1),亞弦的「他們又將說這是燦爛的,馬蒂斯/雙眼焚燬整座的聖母院,自遊戲間/房中的赤裸冉冉上升去膈肢/那些天使/沒有回聲,斑豹蹲立於暗中/織造一切奇遇的你的手拆散所有的髮髻/而在電吉他粗重的撥弄下/在不知什麼夢的危險邊陲/作金色的她們是橫臥於/一條薔薇綴成的褥子上——」(《獻給馬蒂斯》),商禽的「一整天我在我的小屋中流浪,用髮行走。長腳蜈蚣。我用眼行走;有幾公克的燐為此付出代價。我用腦行走。閉眼,一塊磚在腦中運行,被阻於一扇竹門:然后運轉於四壁」(〈事件〉),或是秦松的「鬱之成長,黑之成長/我探求的內部之風景遂展現/……超重的低氣壓下沈,下沈/球狀的意象爆裂於上升/成碎片,成不可名狀知新的意象/乃以心中之眼,透視開向藍天的窗/晨曦之曙光被分割地照射著」(〈黑森林〉)。
五、六十年代視覺式拼貼意象的超現實詩風成為台灣現代詩的發展脈絡中,雖然時隱時顯,卻是始終存在的一條支流。根據洛夫所言,六、七十年代的葉維廉、大荒、管管、辛鬱、楚戈、周鼎、沈臨彬、張默、碧果都是具有超現實風格的詩人(〈超現實主義與中國現代詩〉 4),而至八十年代的新詩人,如蘇紹連與陳黎,也都可看的到超現實的影子。游喚(游志誠)與孟樊都指出台灣新世代詩作承襲傳統最多的,是超現實手法。游喚此說之目的是替現代派詩人辯護,指其在「沈悶的政治壓制氣氛」之下,「透過託喻與象徵,微妙婉轉地超拔在現實外的另一種現實」(241)。而孟樊(陳俊榮)在討論台灣後現代詩的特徵時,指出的魔幻寫實、意符遊戲、精神分裂與拼貼等,都是超現實詩派所凸顯的風格,而林群盛〈愕〉「在池邊散步一低頭胸前的黑色原子筆竟跳進水底而落上來的是一朵黑色的玫瑰」的魔幻寫實,實際上是承襲了六十年代現代詩派如洛夫者的詩風(190-209)。其他如陳黎的〈驟雨〉強行拼貼孟克的畫《尖叫》與達利的畫《記憶的堅持:液化與僵硬了的時間》,〈吠月之犬〉重寫米羅的畫與紀弦的〈吠月的犬〉,〈邀舞〉堆疊梵谷的畫,與楊然的〈下午:讀馬格利特的一幅畫〉都是例子。
超現實畫派的視覺平面上無理性拼貼與夢魘式的氣氛,翻轉了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視角,正好提供台灣五、六十年代詩人新的語彙與文法,以及逃離現實思想箝制的管道。而且,這種新的語彙和文法,是透過跨越不同藝術形式的界線,側面瞥見而得到的靈感。瞥見的靈感有偷取的自由,而沒有系統內承傳的規範或法統。中國大陸三、四十年代以迄台灣五、六十年代保守的視覺藝術傳統之下,前衛藝術家透過日本文藝界的刺激而發展的超現實異端,竟是促進台灣現代詩「橫向」移植挪用視覺藝術、更新語彙及文法的直接觸媒,並造成了台灣現代詩的主流傳統。而若我們進一步檢視台灣詩人及批評家對所謂「超現實」的文字詮釋,更會發現我們可以編撰出一部新的詞典。而這個外來辭彙奇妙地替每一個人執行不同的政治企圖,並揭露了各人潛藏內心的社會他者。至於超現實視角提供的外來文化他者如何為台灣文化工作者開闢抗拒文化認同系統的裂縫,將在下章中繼續討論。
- 此文為國科會專題計劃(NSC84-2411-H-030-002)之部份成果。
中文部份:
王秀雄•〈台灣第一代西畫家的保守與權威主義暨期對戰後台灣西畫的影響〉《中國•現代•美術?兼論日韓現代美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80),135-174。
白荻 • 〈超現實主義的檢討 (一)」, 《笠》 , 2卷3期 ,民54年8月 , 頁42𠳿窖楚C
羊子喬 • 〈超現實主義的提倡者--楊熾昌: 訪楊熾昌談文學之旅〉 , 《台灣文藝》 , 102期 , 民75年9月 , 頁113𠳿陝陝插C
李仲生•《李仲生文集》蕭瓊瑞編,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83。
__________•〈超現實派繪畫〉,原載1955﹒8﹒5《聯合報》六版,收錄於《李仲生文集》蕭瓊瑞編,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83。第25頁。
__________•〈超現實主義繪畫〉,原載1953﹒6﹒10《聯合報》六版,收錄於《李仲生文集》蕭瓊瑞編,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83。第23𠳿悻陪間C
李鑄晉•〈巴黎與中國初期西洋畫的發展〉,《中國𠘚睅丑G早期旅法畫家回顧展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77年,7𠳿陝揚間C
林亨泰•〈台灣詩史上的一次大融合(前期):一九五0年代後半期的台灣詩壇〉,《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民國84年三𠘚迨諢A未發表之論文稿。
__________•〈現代詩季刊與現代主義〉《現代詩》 ,復刊第22期 , 1994年8月 , 頁18𠳿悻間C
孟樊•〈台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世紀末偏航》(台北:時報,1990),145𠳿悻悻鬼間C
洛夫•〈詩人之鏡:《石室之死亡》自序〉,《創世紀》21期,民53年12月,2𠳿陝陛C
__________•〈超現實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幼獅文藝》,民國58年6月號,164𠳿陝楷情C
__________•〈我與西洋文學〉,中華民國第五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座談會,收於《詩的邊緣》。台北:漢光文化,1986。
紀弦•《紀弦詩論》現代詩社,民43。
__________•《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民59。
__________•〈詩是詩、歌是歌、我們不說詩歌〉。四十四年秋,錄於《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民59。
__________•〈六點答覆〉。四十七年五月,錄於《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民59。91𠳿腺陪間C
__________•〈多餘的困惑及其他〉。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錄於《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民59。95𠳿陝砭雁間C
__________•〈從自由詩的現代化到現代詩的古典化〉。五十年夏,錄於《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民59。26𠳿甜戚間C
__________•〈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四十六年,錄於《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民59。159𠳿陝窖痍間C
__________•〈從1937年說起?紀弦回憶錄之一片段〉。《文訊》7/8(1984.2):76-85。
__________•〈三十年代的路易士〉,《聯合報》副刊,民國82年8月28日。
__________•〈在人生的夏天〉,《中央日報》副刊,民國80年12月23日。
柏谷•譯 〈形上學派、超現實派與象徵詩派〉。 Kimon Friar• 《現代詩》 , 35期 , 民50年8月 , 頁22𠳿悻插C
朗紹君•〈中國現代藝術的開拓者〉。《中國前衛藝術》(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64-66。
奚密•〈我有我的歌:紀弦早期作品淺析〉。《現代詩》1(1994.2):4-13.
__________•〈從現代到當代?從米羅的〈吠月之犬〉談起〉。《中外文學》當代詩詮釋專輯,第二十三卷第3期(1994年八月),6𠳿陝痍間C
__________•〈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民國84年三𠘚迨諢A未發表之論文稿。
張默•〈從《靈河》到《魔歌》〉。(1975)收錄於《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台北:漢光,1988),162𠳿陝窖楹間C
張漢良 •〈中國現代詩的 【超現實主義風潮】:一個影響研究的倣作〉。《中外文學》, 10卷1期 , 民70年6月,頁148𠳿陝窖插C
張元茜•〈民初藝術改革的本質?記民初一段特殊的文化史〉。《中國𠘚睅丑G早期旅法畫家回顧展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77年,27𠳿郭楹間C
陳厚誠•《死神唇邊的笑:李金髮傳》。台北:業強出版,1994。
梅漢唐文•(Hans van der Meyden)〈進入國際藝術的大熔爐?中國畫家及巴黎畫派(1920𠳿陝腺揣砥^〉,《中國𠘚睅丑G早期旅法畫家回顧展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77年,16𠳿悻雁間C
商禽•〈閱讀紀弦的詩〉。《現代詩》20(1993.7):32-34。
游喚•「幽人意識與自然懷鄉?論台灣新世代詩人的詩」。《世紀末偏航》(台北:時報,1990),229𠳿悻窖陪間C
趙無極•〈趙無極的自白〉,頁30;引於蕭瓊瑞〈來台初期的李仲生〉《李仲生》,頁21。
葉笛•譯 〈超現實主義宣言〉 Andr* Breton•《笠》,2卷1期 , 民54年6月 , 頁13𠳿甜窗C
__________•「日據時代台灣詩壇的超現實主義運動?風車詩社的詩運動」,《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民國84年三𠘚迨諢A未發表之論文稿。
劉岳兵 •〈詩魔的禪悟•禪學的匯通:試論洛夫詩路歷程中超現實主義〉。 《幼獅文藝》 , 77卷2期 , 民82年2月 ,頁48𠳿揣插C
龍瑛宗•〈熱帶的椅子〉《文藝首都》九卷三號,1941,95至96頁,引於羅成純「龍瑛宗研究」《龍瑛宗集》。台北:前衛,1990。233𠳿甜悻窗C
羅門•〈內在視覺世界的探索?看李仲生教授畫展有感〉。原刊於民族晚報1979年十二月一日,收錄於《論視覺藝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84。
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 1945𠳿陝腺閒砥n台北•東大,1991。
__________•〈來台初期的李仲生:1949𠳿陝腺揣窗r《李仲生》台北:伯亞出版社,1991,頁1𠳿揣窗C
外文部份:
Caws, Mary Ann. The Art of Interference: Stressed Readings inVisual and Verbal Text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9.
Brower, Reuben A. Mirror on Mirror: Thranslation, Imitation, Parod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Krieger, Murray. Ekphrasis: The Illusion of the Natural Sig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__________. "The Ekphrastic Principle and the Still Movement of Poetry: Or, Laocoon Revisited." The Play and Place of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67. 105-28.
Mitchell, W.J.T. "Ekphrasis and the Other." South Atllantic Quarterly 91:3 (1992). 695-719.
__________. "On Poems on Pictures: Ekphrasis and the Other", Poetics Today speical issue, Literature and Art, ed. Wendy Steiner, vol. 10(1989).
__________.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Sullivan, Michael, "Individualism, Protest and the Avant-Garde in Modern Chinese Art" in China: Modernity and Ar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ipei: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1991). 97-118.
FOOTNOTES********************************
{1} 例如Reuben Brower 在《鏡中鏡:翻譯、模仿、擬諷》一書中談到不同形式的翻譯版本時,提出「想像性的重寫」(imaginative re-making, imitation) 、引用 (allusion) 與「積進的翻譯」 (radical translation) 等極端翻譯版本的概念(2)。他認為,不同語言的譯本時常受到當地歷史、當時或前期的藝術、文學、宗教傳統,以及文化與語言的決定。通常,越是自主性的翻譯改寫,對此地文化的更新再生的影響力也就越強。《鏡中鏡:翻譯、模仿、擬諷》這本書中討論幾種不同形式的翻譯,包括同一神話的視覺與文字的不同翻譯改寫版本。如Virgil 的Aeneid, Dryden的Aeneid, Rubens' Quos ego--, Neptune Calming the Tempest。
{2} 此文中本人將著重於視覺翻譯,至於文化轉譯過程中的聽覺翻譯或是影像翻譯,本人會另文討論。
{3} 林亨泰在〈現代詩季刊與現代主義〉一文中,特別以《現代詩》第十三期為例,指出紀弦為了刻意凸出移植說,將大篇幅的譯詩編排在國內創作作品之前,也就是說,該期在紀弦的「現代派信條」、「現代派信條釋義」、「社論」之後,連續自第七頁到第十三頁編排了世界各國現代詩作品的翻譯,第十四頁起才開始刊登國內作品(22)。紀弦本人自該期起也連續翻譯Paul Fort, Guillaume Apollinaire, Jean Cocteau, Pierre Reverdy, Raymond Radiguet, Marie Laurencin, Max Jacob, Yvan Goll 等人的詩。
{4} 比較特別的是,這些詩刊上的譯作多半是出自詩人之筆,如紀弦、方思、葉泥、馬朗、林亨泰、洛夫、葉笛、陳千武、白萩、趙天儀等,而當時最常被翻譯的作家是歐美現代派詩人,如超現實詩人保爾·福爾Paul Fort, 阿保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保羅艾呂亞Paul 邮uard, 羅特阿孟Lautreamont, 許拜維艾爾Jules Superville, 高克多Jean Cocteau, 比艾·勒爾維底Pierre Reverdy, 與象徵意象派詩人,尤其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艾略特T.S. Eliot, 奧登W.H. Auden, 威廉士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
{5} 葉笛近日在《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民國84年三𠘚迨諢^的會議上亦再度口頭說明他所參考的布魯東超現實主義宣言是日文版,並且是節譯本。
{6} 王秀雄認為,此處所述台灣第一代畫家的早期背景,與戰後台灣的長期戒嚴(1949-1988),六0年代因外交受挫而發展的反西化與本土回歸心態,加上日文書籍被禁而受日式教育的畫家無法接受新知等因素,使得這一批元老畫家不再變更畫風,甚而他們控制二十七屆「全省美展」,主導台灣西畫的保守風氣,使得台灣西畫停留在泛印象主義或野獸派之流(169-171)。
{7} 蕭瓊瑞指出李仲生在國內與在日本都沒有能夠進入正式的藝術學院,這是他的反學院本質,也與他日後的非學院式的私人畫室收徒授藝也有關係(《李仲生》9)。
{8} 李仲生晚期的作品中卻有自動技法的明顯痕跡,見《李仲生》一書中所收錄畫作。
{9} 蕭瓊瑞指出,當時合辦美術班的劉獅日後畫風轉為保守,朱德群出國,林聖揚在師大藝術系保守環境中無法發揮,只有李仲生真正對台灣畫壇的現代派產生直接的促成作用(《李仲生》4)。但是,李仲生反對結社,甚至在其弟子成立東方畫會前夕,離開台北,避居彰化二十餘年,莫不是受到白色恐怖之影響。
{10} 東方畫會成立前後,國畫界亦發生革命性的變化。1957年提倡國畫現代化的劉國松及五月畫派脫離省展,展出極具革命性的新國畫展,並且引發正統國畫的論戰,此次論戰吸引了楚戈及余光中等現代詩人加入討論。
{11} 此畫作於民國四十一年,取自《紀弦論現代詩》封面。
{12} 奚密亦曾指出紀弦詩在「語言,語氣、意象、辭彙」方面都和李金髮相近(1994:11)。
{13} 例如「致或人」(未來派)、「散步的魚」(考克多)、「十一月的小抒情主義」(超現實主義)、「夢中大陸」、「構圖」、「畫室」、「色彩之歌」、「夢回」、「吠月的犬」、「等級」、「觀感」等,皆有以繪畫構圖或著色之觀點來作詩的痕跡。
{14} 商禽曾指出「月夜、犬吠」是紀弦詩中重要的象徵符號,是「由詩人的生活中、生命中衍生出來的」,「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夜〉(民23年)、〈寒夜〉(民26年)、〈夜行〉(民33年)、〈絕望〉(民34年)、〈狼之獨步〉(民53年)等(33-34)。
{15} Murray Krieger 在他的新書 Ekphrasis 中,將配合圖像出現的文區分為 epigram, ekphrasis, emblem 。epigram 是銘刻在雕像或畫像旁的文字, Emblem 是需要圖示的文字,而Ekphrasis 是脫離圖畫雕像的文字(Krieger 15)。例如 John Keats 的 "Ode on the Grecian Urn," P.B. Shelley 的 "Ozymandias," Wallace Stevens's "Anecdote of the Jar," W.B. Yeats's "Leda and the Swan," Dante.G. Rossetti's "Lady of the Rock" 等。
{16} 以上討論出自W.J.T. Mitchell (1992) 的文章 "Ekphrasis and the Other"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1:3.亦可參見W.J.T.Mitchell, "On Poems on Pictures: Ekphrasis and the Other", Poetics Today speical issue, Literature and Art, ed. Wendy Steiner, vol. 10(1989); also, Mitchell,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7} Caws 此處借用了Bakhtin 的對話式想像的理論。
{18} 在米羅其他的畫作中亦有梯子的母題,例如 "The Escape Ladder" ( 1940)。然而,米羅畫作中的梯子是幫助畫家逃離地面、通往天空的管道。
{19} 這些詩例中的超現實風格與視覺轉換皆應另外為文深入討論。
{20} 八十年代的超現實風格詩例與其中的視覺轉換也應另外為文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