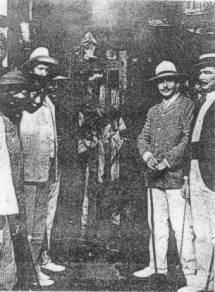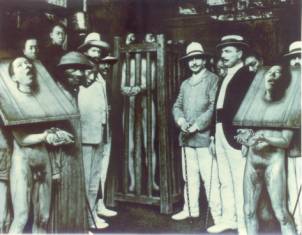『現代性』的視覺詮釋︰ 劉紀蕙 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 2001年11月22日修訂 ****** 在推離的動作當中﹐隱隱浮現狂暴而黑暗的叛逆力量﹐對抗從放縱無度的外在或是內在流瀉出來的威脅﹐朝向超越可能的、可忍受的與可理解的範疇之外驅逐出去。 ---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p. 1 我所關心的歷史﹐是在那被合法性所排除的「歷史之外」的歷史﹐那屬於恍惚的場域﹐如同字詞間連接的空隙﹐一種被隱藏在迷霧中「失語」的歷史﹐一種存在我們語言、肉體、慾望與氣味內的歷史。凝視被排除的歷史﹐如同凝視當代中被隱匿的其他「當代性」﹐兩者間是必需相互挖掘。……殘酷﹐常讓我們被擋在影像之外﹐然而傷口闇黑的深淵﹐不是讓我們穿過的裂縫嗎?一個可能穿過「棄絕」的裂縫。 ──陳界仁﹐<招魂術︰關於作品的形式> ***** 關鍵字:台灣當代藝術、陳界仁、前衛藝術、恐怖美學、現代性、視覺文化、精神分析、心態歷史
我書寫這篇論文的主要企圖,是要展開面對歷史而進行的精神分析式閱讀的方法論。在《太初有愛﹕精神分析與信心》(In the Beginning Was Love)一書中,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曾經指出,精神分析的對象是情感轉移與反向轉移(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的往復過程之中的語言交換。在精神分析式的閱讀中,字或是圖像語彙的表面指涉意義並不重要,歷史事實亦並不佔據決定意義的絕對位置,重要的是要捕捉文字或是視覺的象徵形式中所流動與交換的幻想,以及此符號運作底層的文化衝動,也就是我在本文中將要討論的「真實」(the real),或是「精神現實」(psychic reality)。面對文化場域的文本時,我們探討的便是此符號背後的趨力,以及此符號構織中不同位置的說話主體,受難中的主體,邊緣狀態的主體﹐並且試圖捕捉居於不同歷史與文化時刻的幻想、歷史經驗以及其所呈現的症狀。 我所選取的研究對象,是牽涉了現代台灣與中國歷史創傷時期的視覺再現文本。對於「創傷」,克莉絲特娃曾說,這是象徵界與內在欲力衝動之撞擊而產生的斷裂,而「精神分析過程」是協助主體尋回語言的過程(Kristeva: 1995, 71)。根據克莉絲特娃的說法,進行精神分析式的閱讀或是理解,是以理解(understanding)與同感心(empathy),進入情感轉移與反向轉移的關係,讓自己的心理衝突與無意識內容得以被呈現,並且以相似的心理經驗,誘引病人發展同樣類似的心理經驗,展開可以互動的話語(compatible discourse),而使被分析者採取使用語言的陽性主控位置(Kristeva: 1995, 78)。如此說來,面對歷史的精神分析閱讀與對話,便是批評者/分析者協助對話對象(包含文化、社群、以及自身)面對歷史創傷經驗以及此創傷所導致的意識斷裂,尋求語言,以便使得被壓抑與遺忘的狀態,能夠透過語言的轉移,進入意識以及語言的層次,而得到某種與歷史的和解。 這種精神分析式的對話,不是理性溝通或是立場陳述,而是情感式(affective)的「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在書寫中,我們與文學藝術進行精神分析式的對話,並且透過這種情感轉移而達到有同感效應的互為主體,開始向此系統開放。在認同、情感轉移以及透過語言而「說出來」的過程中,我們也翻譯出了不同的主體位置,經驗多種主體聲音以及主體轉換的過程,從而帶出我們自己的經驗歷史。藝術家的創作,是一種精神分析的過程;而我們面對文學與藝術的對話與書寫,也是一種精神分析的過程。透過這種與歷史對話的語言,我們自己的精神現實也逐漸復甦。 從台灣當代前衛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藝術家透過視覺圖像進行對於「中國/台灣」現代化進程的批判與詮釋。陳界仁在作品中挑選了幾個充分顯露現代化進程中體制性暴力的創傷性時間節點。體制性的暴力展現於建立清潔與病態的區分,以及清除異己的工程,例如清黨、內戰。此清除異己的心態,便成為文化中普遍的恐懼症,恐懼不熟悉而非家的異質物。因此,這些暴力運作的時間節點更造成了歷史的斷裂,也就是政治結構轉變之後歷史詮釋與歷史累積的斷裂。這種斷裂,實際上是透過知識系統與認知模式的體制性斷裂所完成。基於此體制性斷裂,中國/台灣對於現代進程中諸種現象展現了詮釋的片面與認知的斷層,此斷層也同時造成了台灣的「當代」文化狀況。 因此,面對台灣的「當代」,觀察其中所鑲嵌的歷史斷裂與認知體系肢解的時刻,展開精神分析式的對話,思考台灣的文化問題,便是我此文所進行的工作。 ***** 台灣當代藝術家如何以圖像思維的方式理解與書寫當代社會與台灣文化?如何透過圖像來詮釋累積銘刻於當代的歷史?而我們要以何種方式將此視覺文本視為文化研究的對象﹐視為文化事件,以何種方法論進行分析與詮釋?我們要如何根據此文化事件與視覺想像模式來捕捉其中所呈現的台灣特殊歷史經驗、文化場域以及複雜的心態史? 我要從台北市立美術館於一九九八年展出的二二八紀念美展中陳界仁的《內暴圖1947-1998》,以及與此作品相關的二二八紀念美展系列,作為一個切入點﹐開始我的討論。台北市立美術館從一九九六年陳水扁市長主持市政之下﹐開始了連續四年的二二八紀念美展﹐直到一九九九年暫時告一段落。[1] 無論是一九九六年展覽中所強調採用二二八事件當事人的「作品、史料」﹐以及當年的「文件、照片」(林曼麗 6)﹐一九九八年陳水扁市長要求「將創作內涵﹐拉回事件本身﹐要求藝術家正視事件、進入歷史情境之中」(陳水扁 4)﹐或是一九九九年展覽的策展者所強調的「重塑歷史現場與歷史圖像」(施並錫 11-12)﹐我們都可以看到依附「史料」與「見證」歷史的敘述動力。[2] 這種回到歷史現場的敘述模式﹐決定了一種理解歷史的角度。一九九八年周孟德的《雲變》﹐是上述的歷史現場敘述模式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3] 我們看到的是對於歷史事件的描述與立場的宣稱。 圖一:周孟德《雲變》(左圖) 圖二:陳界仁《內暴圖1947-1998》的裝置場所(右圖)
同年展覽中陳界仁的《內暴圖1947-1998》﹐則與上述歷史事件描述與立場宣稱的作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表面上﹐陳界仁的作品似乎呈現了殺戮事件的殘暴圖景:在放大的巨幅電子影像前﹐觀眾站在兩面牆壁鑲嵌的石碑之間﹐聽到四周傳出模糊隱約的人聲﹐恍如置身於地獄之中。但是﹐當觀眾仔細觀看這幅作品﹐卻會立即意識到此圖像展露的荒謬、瘋狂、誇張與非寫實,同時卻又會令人十分不安﹐就如同James Elkins所說的﹐似乎這個我們注視的對象向我們回望逼視﹐我們看到了「我們知道不能夠或是不應該看到的景象」而必須將目光轉開(Elkins, 115)。 圖三:陳界仁《內暴圖1947-1998》
這個圖像中﹐陳界仁利用電腦合成影像的方式﹐在前景置放一個擬真的屍體﹐這個將頭轉向背景﹐雙手執著被斬斷的頭顱﹐斜斜地望向我們﹐形成了一個死亡符號﹐一個momento mori﹐以一種過去式的姿態﹐提出了一個難以解決的有關殺戮與死亡的模糊問題﹐一個屬於「寫實」場域的問題:是誰殺的?如何進行?為什麼會發生?後來呢?誰該負責任?中景的圖像卻是三對以藝術家自己作為模特兒﹐搬演出自相殘殺卻充滿如同嘉年華會一般過度而誇張的歡愉場景。因此﹐前景的死亡符號所提出的「寫實」問題﹐被中景的圖像修飾對照﹐而形成了一個較為具體的問題︰死亡發生之前的殺戮場景所執行的暴力動作﹐是否也同時指向自身?而且是自虐而自殘自毀的﹐其中甚至激發著極度的快感?這個問題﹐則脫離了「寫實」場域﹐而進入了「真實」的面向。令我們不安而無法直視的﹐就是這個「真實」。 然而﹐是什麼「真實」?為什麼陳界仁將這樣的問題放到二二八的紀念美展中?為什麼他將此作品的標題定為《內暴圖1947-1998》?從一九四七到一九九八﹐有什麼內在的暴亂持續在發生當中?從這樣的圖像中﹐我們能夠觀察到什麼樣的歷史詮釋以及主體位置? 或許我們需要回到陳界仁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的「魂魄暴亂」系列﹐試圖釐清陳界仁有意展開的計畫﹐以及我們從他的圖像中﹐能夠閱讀到什麼其他的問題﹐例如﹐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真實」。 陳界仁從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完成了一系列被他稱呼為「魂魄暴亂」的作品︰《本生圖》(1996)﹐《去勢圖》(1996)﹐《自殘圖》(1996)﹐《法治圖》(1997)﹐《失聲圖》(1997)﹐《恍惚相》(1998)﹐《連體魂》(1998)﹐《哪吒相》(1998)﹐《瘋癲城》(1999)。陳陳界仁的「魂魄暴亂」系列Revolt in the Soul & Bdoy在過去幾年間曾經受邀在世界各地展覽﹐包括一九九九年威尼斯的雙年展。[4] 不過﹐陳界仁的作品被西方世界注意的原因﹐與他的作品對於台灣觀眾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對於「恐怖美學」的興趣﹐以及對於「中國式酷刑」(supplice chinois)的好奇﹐從Mirbeau一八九六年所寫的Jardin des supplices, 以及Matignon, Bataille, Lucien Bodard等人所提出的施虐快感之美學層面問題﹐已經充分展現。[5] 但是﹐在陳界仁的作品中﹐這些「殘酷美學」則被轉化為他對此西方式好奇的嘲諷批判﹐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同時將此施虐快感置換為他對中國現代化歷史中建國工程的體制性宰制快感的批判詮釋。 陳界仁自己曾經說明︰[6] 這一系列的作品是要試圖重新檢視中國到台灣的現代化歷史發展中﹐刑罰與暴力從其外顯的形式如何轉變到其隱匿的形式。這種刑罰形式的轉換和中國與台灣的「現代性」有密切的關連。陳界仁將一九○○年到一九五○年設定為「史前史」﹐也就是他出生之前的現代化過程中的刑罰史︰從清朝即將終止的最後的酷刑、[7] 國民黨革命、清黨、內戰、到霧社事件﹐「排除」的機制以不同的形態呈現﹐《本生圖》﹐《去勢圖》﹐《自殘圖》﹐《法治圖》﹐與《失聲圖》這幾個作品﹐就屬於這個「史前史」。陳界仁的策略是﹐選用幾幅歷史照片﹐扭轉其中的觀視角度﹐藉以檢查幾個刑罰階段所牽涉的歷史脈絡。以歷史照片出發﹐對陳界仁來說﹐是面對現代化過程中觀看與被看﹐或是權力操控與受控相對位置的最佳媒介。陳界仁認為﹐一九五○以後﹐直到當今﹐刑罰與暴力已經不斷被內化﹐而透過各種機制以隱匿的方式呈現。因此﹐在這一系列的作品中﹐例如《恍惚相》﹐《連體魂》﹐《哪吒相》﹐與《瘋癲城》﹐影像中的場景便不再以歷史照片為依據﹐而完全出自於他虛構的想像。一九九八年顯然是陳界仁創作的轉變期﹐前面所提的《內暴圖1947-1998》﹐便是此系列的轉折點。 圖四:左圖是《本生圖》所依據的照片﹐取自巴代耶 (Georges Bataille)《情慾的淚水》(Tears of Eros) 圖五:右圖是於天津印行的「中國酷刑系列」第三號明信片﹐蓋有一九一二年7月9日天津郵戳﹐取自《舊夢重驚:清代明信片選集》。
《本生圖》是「魂魄暴亂」系列的起點。這幅圖是陳界仁取自巴代耶 (Georges Bataille)《情慾的淚水》(Tears of Eros)中引用的一幅照片。[8] 原本這幅照片的取景﹐凌遲的行刑場景﹐是基於西方人類學式以及觀光旅遊式的好奇與興趣﹐所要引發的觀看位置﹐自然也是個「西方/外來者」的位置。此種「人類學+觀光旅遊」﹐或是「報導+販賣」的觀點﹐的確成為二十世紀初期此類圖像明信片大量印行的賣點﹐並且廣泛在西方人士之間透過書信郵寄而流傳。[9] 這些充滿異國風俗的明信片﹐由西方人購買﹐從中國寄到世界各地﹐是一種記錄時代的特殊形式。 圖六:陳界仁《本生圖》
陳界仁則利用此類吸引西方興趣焦點的圖像﹐透過電腦繪圖加以改變﹐放大圖像的框架﹐複製受刑者的頭顱﹐將巴代耶書中描繪的「極度恐怖與狂喜」之表情轉換成為一個不可置信的過度陳述﹐擾亂了西方觀眾要滿足視覺消費的好奇心理。圖像中﹐陳界仁在背景左後方放置了「他自己」的影像﹐並且以旁觀者的姿態﹐與其他歷經現代化過程的中國人與西方人﹐一起目睹並參與此酷刑的執行場景。這個插入的「現代」目光﹐更將原本照片中的歷史時刻問題化。這是個陳界仁式現代化詮釋版本的起點。透過相片之框架內外這些複雜的交錯目光﹐這幅相片所揭露的﹐不僅是中國最為古老的酷刑習俗──凌遲,而更是西方現代技術──攝影/觀看──介入中國所造成的極具諷刺力的歷史時刻。 圖七:左圖﹐陳界仁《去勢圖》所依據照片﹐攝影者不詳﹐亦刊於《中國攝影史》﹐56頁。陳界仁提供。 圖八:右圖﹐陳界仁《去勢圖》 《去勢圖》[10]延續《本生圖》的主題﹐凸顯「西方」觀看「中國」的奇特興趣。不過﹐視覺上﹐此圖像的構圖與《本生圖》造成極大的對比。《本生圖》中﹐所有的目光都環繞著被行刑的犯人﹐更正確的說﹐環繞著行刑者施行凌遲的動作。似乎在期待中﹐這些人同樣經歷著一場驚悚的過程。《去勢圖》中﹐行刑者、外國領事以及圍觀者則都擺好姿勢﹐排成一列﹐並且將目光聚集於攝影機的鏡頭。這種邀請觀者觀看自身所曾經目睹而參與過的驚悚場景﹐使觀者的興趣集中在囚籠中的犯人以及四周服飾整齊好整以暇的外國人以及圍觀者的對比之上。其實﹐真正令人驚悚的過程以及場景﹐都已經被隱藏在暗處的囚籠中。 陳界仁在《去勢圖》中所作的處理﹐則是以自己為模特兒﹐將原本被隱沒在囚籠中的囚犯﹐複製影像﹐放置於照片前景的左右方﹐背景左方再加上兩個不同年紀的「陳界仁」﹐觀看此場景﹐形同前後圍繞著的觀看框架。這種做法﹐就如同翻開衣服的內裡﹐露出破綻內的棉絮﹐或是掀開發膿的傷口﹐展露膿瘡的實情。此處的翻開衣服內裡,或是掀開發膿傷口,是陳界仁面對歷史場景所採取的重要換喻模式︰傷口本身並不是重點,陳界仁真正要揭露的,是揭開傷口表象之內的歷史真實。 陳界仁在《本生圖》與《去勢圖》所作的圖像處理﹐將現代化過程中歷史時刻的諷刺性凸顯了出來。中國的原始﹐以最為古老的酷刑圖像呈現;而西方的文明科技﹐則以攝影技術展現。中國的現代化﹐因為西方的介入──西方的科技、軍事力量、商業機制以及具體執行的租界區﹐而被迫加速過程。依照陳界仁的詮釋﹐中國被迫接受西方介入的現代化進程﹐便如同凌遲﹐或是去勢﹐透過科技﹐中國的主體位置一點一點的被削減。 不過,如前文已經提及,陳界仁作品中的這些「殘酷美學」時刻,其實都被轉化為他對此西方式好奇的嘲諷批判,以及對於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反省與批判。「魂魄暴亂」中的《本生圖》與《去勢圖》是這個反省現代性的起點;《自殘圖》、《失聲圖》與《法治圖》中,陳界仁則將這些殘酷時刻中的施虐快感置換為中國現代化建國工程中的體制性宰制快感。也就是說,陳界仁開始面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排他系統,並且針對國家建構下體制性的暴力以及族群自殘的歷史進行批判與詮釋。 圖九:左圖﹐陳界仁《自殘圖》左半邊所依據之照片。攝影者不祥﹐東北清黨照片﹐陳界仁提供。 圖十:右圖﹐陳界仁《自殘圖》右半邊所依據之照片。Jay Calvin Huston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時期在廣東所拍攝的照片﹐陳界仁提供。
陳界仁在《自殘圖》中﹐利用電腦剪輯﹐將兩幅照片並置:此圖的左半邊大約是一九二八年在東北所拍攝的照片﹐根據陳界仁的說法﹐是張作霖清黨時期所拍攝的﹐右半邊則是Jay Calvin Huston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時期在廣東所拍攝的照片。 圖十一:陳界仁《自殘圖》
陳界仁再度將自己作為模特兒﹐替換圖片中被砍頭的犯人﹐並且加上一個自相殘殺的連體人。此外﹐圖片的左後方背景有一個「陳界仁」在觀看此屠殺場景。《失聲圖》中﹐陳界仁則將以刀刃自殘而極度歡愉的圖像並置於遍地橫陳的屍體上﹐此歡愉的自殘者/「陳界仁」自圖像中心望向我們。這根據陳界仁的說法以及他創作的意圖﹐這個如同地獄景象的陳屍所﹐是要揭露國民黨在內戰期間佔據延安後﹐屠殺民眾所造成的景象。陳界仁的計畫是要呈現國民黨在清末革命成功之後﹐卻以反革命的方式進行政變與內戰﹐迫害殘殺左翼﹐並且牽連無辜民眾。但是根據提供圖片的中央通訊社資料﹐這幅照片是一九四六年內戰期間共軍佔領崇禮後﹐屠殺全村﹐所留下的記錄。[11] 因此﹐陳界仁試圖揭露右翼的暴行,卻不意反而同時揭露了左翼的殘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左翼與右翼以一致的方式,各自進行排他性的暴行﹐經由刑罰/排除/肅清的工程而達到鞏固權力的位置。 圖十二:左圖﹐陳界仁《失聲圖》所依據照片﹐一九四六年內戰期間崇禮事件﹐中央通訊社1946年12月照片(#2100)﹐陳界仁提供。 圖十三:右圖﹐陳界仁《失聲圖》
《法治圖》則更利用霧社事件原住民不同族群自相屠殺的歷史照片﹐加上陳界仁自己扮演的日本軍人、旁觀的原住民、中央被行刑的原住民﹐以及一些散置地面的頭顱﹐凸顯此事件的內在矛盾。[12] 圖十四:陳界仁《法治圖》
在陳界仁的圖像書寫中﹐呈現了一種中國現代化之恐怖時刻的史詩面貌。這個歷史進程﹐從凌遲與去勢的酷刑﹐到黨派族群自相屠殺﹐都是向自己施加暴力的機制。因此﹐無論這些歷史照片的真實場景是什麼﹐陳界仁都一再將自己複製﹐甚至以連體人的方式出現。在每一個歷史時刻加上自己的印記﹐就是要凸顯此族群間排除暴力的自我分裂與瘋狂﹐以及此歷史時刻在我們身上銘刻的痕跡。這是個較為複雜的問題﹐我要在此文章的後半部繼續討論此問題。 相對於前面所討論的歷史圖像﹐陳界仁的「魂魄暴亂」中的第二階段﹐則都是沒有歷史照片作為依據的虛構場景。如果一九五○年以前是陳界仁所說的「史前史」﹐那麼﹐他所面對的歷史就是「戒嚴史」了。「戒嚴史」的階段中,暴力不再以外顯的方式呈現﹐而是透過國家機器施展其控制力量。這一系列虛構場景﹐呈現了陳界仁所謂的被遮蓋、被肢解的歷史所造成的體制性隱匿暴力:《恍惚相》中無頭的神祇在屍首散置的荒原中﹐由兩個瘸腿斷腳而目盲的信徒抬著;《連體魂》呈現毀滅與生機存於一線之隔的時機;《哪吒相》呈現的是被中年人監控的少年犯;《瘋癲城》則是一個婚禮與喪禮同時進行的荒誕怪異景象。 圖十五:左圖﹐陳界仁《恍惚相》;圖十六:右圖﹐陳界仁《連體魂》
圖十七:左圖﹐陳界仁《哪吒相》;圖十八:右圖﹐陳界仁《瘋癲城》
從陳界仁的系列圖像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他的美學邏輯。以圖像的歷史位置來說,陳界仁的暴力圖像既可安置於西方巴代耶式的恐怖美學脈絡,亦可放在中國地獄圖像的視覺脈絡。然而,他與此二種脈絡都保持了距離︰他一則進行了對西方恐怖美學的批判,再則藉著延續中國地獄圖的傳統,卻將其「現代化」──以現代的圖像「翻譯」此地獄圖傳統。陳界仁以歷史照片為本,是有特殊意義的︰拍攝歷史照片者﹐必然與權力操縱者有共謀的位置。從《本生圖》、《去勢圖》、《自殘圖》、《失聲圖》到《法治圖》﹐從檢討西方科技/觀看的介入中國﹐到國共兩黨排除異己的暴力﹐以及霧社事件族群之間在殖民政府慫恿之下而相殘的弔詭關係﹐都牽涉到了權力的操縱位置。透過檢查歷史中被記錄與生產的記憶﹐我們會望見其中隱藏的權力位置﹐以及歷史中被遺忘與排除的那一刻。因此,所謂的「中國的現代化」,對陳界仁來說,與其說是西方的介入,不如說更是中國建立新國家時所強制執行的各種權力操控與排除的機制。我們因此清楚的看到陳界仁透過玩弄凝視觀點的策略﹐也展開了他的圖像批判計畫。 關於攝影與權力位置的牽連﹐陳界仁曾經說過:
於是﹐藉著圖像﹐陳界仁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誰有權力記錄或是複述歷史?他使用什麼樣的工具或是機器操作此記錄歷史的工作?他所預設的觀看/閱讀歷史的人是誰?記錄歷史與觀看/閱讀歷史者的權力關係是什麼?這種記錄歷史的方式如何控制了觀看者的觀看模式?在被支配與被生產的記憶之下﹐什麼樣的歷史被排除與遺忘了?在這套傅柯式的歷史考掘以及觀看位置/權力機制的檢查之外﹐我們也注意到他要呈現的是: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權力鞏固工程所施行的排除機制﹐也就是在冷戰與戒嚴時期被壓抑的中國現代化/建國歷史﹐以及此排除壓抑機制內在牽動的如同施虐者近乎瘋狂的操縱快感。 然而﹐閱讀陳界仁的影像﹐除了他有意鋪陳的圖像批判計畫﹐我們注意到其中還有其他的訊息。我們要如何捕捉陳界仁的圖像批判計畫與他不自覺流露出的其他訊息與意圖之間的落差呢? 對於凝視歷史的經驗﹐陳界仁以文字描述:
當他以電腦光筆在數位板上繪圖時,他感受到了以自己的肉身參與歷史的恍惚狀態:
在陳界仁自己宣稱的圖像批判計畫﹐與此處告白式的幾段札記中﹐或是在他的批判計畫之文字陳述與他的圖像之間﹐其實有著不可忽略的斷裂。陳界仁以自己飾演施虐者的位置﹐目的是要批判權力操縱者排除工程中的狂暴快感﹐但是﹐陳界仁似乎承認﹐透過凝視此「歷史時刻」﹐他還看到他與其他主體位置交互穿梭﹐以及「那一刻」同時滲透在他體內。於是﹐除了檢查歷史中被記錄與生產的記憶﹐其中隱藏的權力操縱位置﹐以及遺忘與排除歷史的那一刻﹐我們也讀到了陳界仁對於「受難時刻」的迷戀﹐以及他以身體參與的方式回到受難場景的衝動。 因此﹐陳界仁「魂魄暴亂」中的圖像引起我興趣的﹐其實不是其「寓意」﹐而是其中展現的「症狀」﹐或是被壓抑排除的記憶之復返與展演。也就是說﹐在陳界仁有意地進行中國現代化的批判工程之同時﹐他也無意地展現了他強迫性回到創傷場景的症狀。此症狀將「魂魄暴亂」中第一階段改寫歷史照片之批判工程背後所隱藏的受難慾望也揭露了出來;在「魂魄暴亂」的第二階段﹐我們更看到了鑲嵌於陳界仁身上回到歷史創傷場景的自殘衝動。這是一種自我掏空、無對象性的自殘與憂鬱狀態。第一階段的作品中那種激怒與狂喜合併的凝視與挑戰已經消失﹐在第二階段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那種基進的目光﹐而只看到傷口的內部。正如同Hal Foster所說﹐當政權急速轉移而信仰喪失的年代﹐藝術家可能會充滿著伊底帕斯式的反叛與攻擊﹐企圖將此象徵秩序/意象-屏障(symbolic order / image-screen)擊毀﹐再則可能會企圖挖掘「表象背面真實的醜陋客體/凝視」(“the obscene object-gaze of the real”) (Foster, 156)。因此﹐在此混亂而迅速改變的轉折過程中﹐藝術家「或是處於相信象徵秩序可能瓦解的狂喜中;或是處於絕望而恐懼的狀態中﹐陷入憂鬱狀態」(Foster, 165)。此處,我們便面對了時代轉型的問題。 憂鬱的起因﹐若要借用克莉絲特娃的說法﹐便是因為原初對象的失落﹐卻無法哀悼。無法哀悼的原因﹐是因為此對象已經被內化。然而﹐此對象的確已經死去﹐如同太陽轉變為黑色﹐而無法繼續投注愛戀﹐因此﹐對於此對象的攻擊性﹐便轉而朝向自身。政治或是宗教偶像之瓦解墜落的時代,容易觀察到此憂鬱之狀態 (Kristeva: 1989, 8)。[13] 翻閱陳界仁同時期的台灣藝術家作品﹐楊茂林、侯俊明、吳天章等人的作品最能夠展現解嚴前後的伊底帕斯式反叛與攻擊;而鄭在東與後期的侯俊明﹐則顯示出後解嚴時期與陳界仁類似的憂鬱與自殘暴力﹐一種朝向自身的攻擊。[14] 從陳界仁的圖像批判﹐我們會提出的問題是︰以陳界仁所說的「經歷歷史被肢解、凌遲」的當下認知狀態﹐觀看歷史者要從何而得知自己被體系化遮蔽的認知?從陳界仁的症狀展演﹐我們則必須繼續問:陳界仁圖像中的自殘與受難衝動以及憂鬱狀態向我們展示了什麼樣的歷史狀況?冷戰與戒嚴時期結束之後﹐或是看似結束﹐其實尚未結束﹐我們如何面對台灣社會文化中承載此認知隔離的效果?這種累積的隔離肢解效果如何以身體化的症狀方式出現於社會的角落中? 在陳界仁的圖像中﹐除了他所要揭露與批判的意圖之外﹐我們其實也看到了他被「創傷」所捕獲、箝制而迷戀的狀態。從他這一系列的第一幅作品《本生圖》﹐到最後的《瘋癲城》﹐我們注意到﹐真正引起他興趣的﹐不是「觀看」角度的諷刺位置﹐而是「傷口」本身。陳界仁說:
真正要讓陳界仁穿越的﹐就是這些闇黑的深淵:身體上的裂縫──利刃割裂的肌膚、橫斬的頭顱、斷黜的手腳、血肉模糊的器官﹐以及糜爛生膿的皮肉。
我必須開始以後設的方式檢討我所使用的方法論。我所面對的問題起點,是台北市立美術館自一九九六年開始持續四年的二二八紀念美展。我將此系列展覽視為一場連續的文化事件。在後解嚴時期,當執政黨與在野黨共同以大量的「台灣意識」、「歷史情感」作為訴求,試圖重塑歷史圖像,以便凝聚與召喚「生命共同體」的想像模式,[15]我們看到了這些畫作以各種宣稱或是描述的方式重新敘述歷史。但是,不同於二二八系列展覽的歷史寫實模式,後二二八世代的陳界仁以最為曖昧而複雜的情緒,展演了他以症狀的方式生活於此歷史中的狀態。 討論歷史記憶時﹐一般人會在寫實的文字或是圖像中尋找能指所承載的歷史痕跡。Jacques le Goff曾經指出﹐若要探討一個時代的心態史﹐面對當時人民的思考模式、主體性與認同的複雜狀態﹐只從文字資料或是主導意識形態來檢查﹐是不夠的。歷史環境與意識形態無法完全說明當時社會文化所產生的次檔案﹐或是視覺圖像與藝術所依循的符碼。Jacques le Goff建議要進入更為細節的小系統(local systems)﹐以便在大系統之外﹐尋求不同的解釋方案(174)。這種對於心態史的複雜認知﹐我完全同意。不過﹐我要提出進一步的看法︰除了歷史時期的主導意識形態與各種小系統會造成表義與詮釋的歧異之外﹐圖像構成本身所具有的「負面」狀態﹐[16] 更可以具體提供我們有關主體對於歷史的複雜態度。 「負面」的底層意義﹐便是如弗洛依德討論無意識狀態時所引用的暗喻一般﹐像是底片一般﹐無意識狀態在顯影之前便已經以結構的方式存在。呈現於意識的意念或是圖像﹐已經是經過轉移而投資的意念與圖像。因此﹐這個「負面」層次就是一種基礎結構﹐以表面不相關卻遙遠相連的辯證方式依存。任何視覺化與形式化的符號過程﹐都有其轉移投資之前的欲力。我此處所討論的圖像構成之負面狀態,便是延續此種理解﹐並且展開此暗喻系統﹐討論「負面」書寫在文化場域的意義﹐翻轉所謂圖像「正常書寫」的單向度結構﹐檢視其如同衣料反面底襯之複雜鉤織紋理與色澤。此「負面」狀態,或是「症狀」的底層結構,可以讓我們瞭解主體性的複雜面向與歷史痕跡。 我曾經以「症狀」的概念﹐來討論我們被固著而僵化的認同想像。[17] 以近二十年的台灣文化場域為例﹐面對於「中國」或是「台灣」﹐依著文化認同的轉向﹐「超我」系統隨著「父祖」在政治或是文化場域具象化方式的改變﹐而形塑出不同軸線的穩定認同架構與意義體系﹐許許多多的小對象/小客體也被以一種偏執的變態姿勢緊緊依附;相對於此超我系統而無法同化的不潔之物﹐則都如同污穢廢棄之物﹐必需被推離排除。因此﹐無論是龐大而同質的淨化系統﹐或是狂亂瘋癲的反社會行為﹐都是我們的症狀︰我們隨著中國或是台灣﹐或是各種變化發生出的系統﹐而延伸出的症狀! 「症狀」﹐如同表演﹐也如同夢象徵﹐是一個符號化的過程。表面的視覺化形式﹐不見得能夠讓我們「看到」符號背後的「意義」或是「所指」。就像是弗洛依德所說﹐「症狀」是以一種表面不相關但卻是遙遠相連的方式﹐壓抑內在慾望﹐卻同時也滿足慾望展演自身的衝動。在症狀中﹐符號選取投注的主觀位置中,我們可以「聽」到主體內在的動力「大聲吶喊」(cries out loud), 或者﹐我們應該說﹐是主體位置意識之外的他者狀態(other, alter)的吶喊。 我在這篇論文中所處理的﹐便是在視覺文化中試圖檢視圖像構成所牽涉的不在場對話對象以及負面論述模式﹐並且尋求一種面對台灣社會文化中以身體化的方式所展現之圖像/症狀的方法論。 圖像文本如同書寫﹐銘刻著藝術家的主體位置。我們必須將圖像當作句子一般來閱讀。[18] 然而﹐就如同克莉絲特娃與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明的互文狀態(intertextuality)﹐[19] 在陳界仁的圖像中﹐我們看到了複雜的句子群組﹐穿插著許多修飾性的附屬子句﹐許多不連貫的片語修辭與斷裂的意象﹐各自牽連著歷史文化與社會的層層脈絡﹐牽動著發言者沒有說出來的位置﹐以及隱藏的對話對象。除此之外﹐我們更在這些複雜「句子」中﹐看到了「向我們迎面擊來並且刺穿我們」的「刺點」(Punctum) (Barthes: 1981, 26)﹐這是具有歷史脈絡與社會狀況而刺痛我們的刺點﹐具有喚醒與回溯創傷經驗力量的刺點。 意象與症狀之間﹐是如同佛洛伊德所說的﹐都屬於「無意識的生產」﹐具有「無意識的同一性」(unconscious identity)﹐而且以「象徵對等」(symbolic equation)的方式轉移。這些轉移的原則,就是類似於壓縮、置換、扭曲、變形的暗喻邏輯(metaphorical),使所選取的對象(符號,症狀)與原本的對象類似卻遙遠而不相干,以便避免被檢查而禁止。因此,佛洛伊德說,所有的症狀,或是符號,都如同「兌換幣」(token)一般,執行經濟交換的過程。[20]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閱讀波特萊爾的《惡之華》﹐讀到了其中的現代震驚經驗所產生的症狀。波特萊爾的詩﹐班雅明認為就是波特萊爾的症狀﹐可是﹐除了這是他自己對於現代性的詮釋之外﹐那也呈現了班雅明自己的創傷經驗。閱讀陳界仁的圖像﹐我們同樣的一則看到了他的詮釋﹐也看到了他的創傷經驗與症狀。 在此﹐我們需要藉由精神分析對於創傷、症狀與昇華的討論作進一步的思考﹐以便掌握此精神分析論述對於文化研究詮釋工作的方法論﹐以及我們要如何面對陳界仁前衛藝術中暴力與死亡的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先回到佛洛伊德所討論的創傷與症狀的問題,我認為也就是符號化的起點。佛洛依德對於創傷經驗的說明是:「一種經驗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心靈遭受到非常高度的刺激,以致無論用接納吸收的方式或是調整改變的方式,都不能以常態的方法來適應,結果使心靈的有效能力之分配,遭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之為創傷的經驗」(Freud: 1917/1932, 264)。佛洛依德還說,「創傷的」這個辭彙除了「經濟的」意義之外無他,也就是說,心理歷程中主體無法應付當時驟然發生的巨大深刻經驗,因此以固著的方式停留在當時發生事件的場景,強迫性地反覆演練修正。這也就是「症狀」的產生。強迫性行為的背後有一種極大的力量在推動,此推動趨力匯聚於「症狀」處;這種心力的集中有如生死交關,而完成的是一種轉移或是交換替代。症狀本身既滿足內在的性慾,亦阻抗此性慾之滿足(Freud:1917/1932, 250-51)。因此﹐症狀正是符號化的過程。在文學與藝術範疇的符號化過程,則是佛洛伊德所說的「昇華」。兩者之間,有內在的關連。 André Green討論昇華的問題時﹐指出佛洛伊德的「昇華」理論中「非性化」(desexualization)的面向,是朝向死亡衝動的動力。佛洛伊德指出昇華與自我理想(ego ideal)以及超我(super-ego)關係密切︰「情慾力比多轉化為自我力比多﹐是放棄性目的之非性化過程。……自我將對象投注的力比多捕捉住﹐並且將自身設定為其唯一的愛的對象﹐使「它」(it)的力比多能量非性化或是昇華,如此﹐自我所進行的工作是朝向「愛欲」Eros目的之對立面﹐並且使自己服從於相反的本能衝動。」 (Freud: 1923, 46)[21] 這種昇華的工作就是與父親典範認同而將原初的情慾解消,甚至以攻擊性的方式釋放死亡慾力 (Freud: 1923, 54-55) 。Green指出﹐這是Eros的結合動力所同時展開的負面作用,也就是他所謂的Neg-sexuality (222)。 Green認為,Winnicott繼續佛洛伊德的理論﹐透過「文化對象」(cultural objects)的概念解釋文明過程以及創造性,而將文化經驗放置於精神拓璞學之內。對於Winnicott而言,「文化對象」是外在現實與內在現實的中介區域,此中介區域同時也是提供必需性對象以及過渡作用的場所(235)。因此,Green延續此對象的「尋找-創造」,客觀的感知(found)與主觀的對象(created)的關連﹐發展出他所稱呼的「對象化功能」(Objectalising Function) (236),這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為趨力尋找對象的「昇華」(237)。Green認為藝術中建立距離之下無接觸的觸摸,就是此既迎且拒的關係。因此,他將昇華定義為在精神與生理的生死欲力拉拒之間的負面工作,或是在對象化與去對象化之間往返(240)。 克莉絲特娃則延續此脈絡﹐繼續發展她對於前衛藝術的研究﹐但是﹐她認為﹐與其說前衛藝術的昇華是超我對於父親的攻擊形式﹐不如說是「弒母」行為。克莉絲特娃認為﹐詩語言便是在語言中建立對象﹐以便替換其所攻擊的象徵秩序﹐並且以此對象的語言物質性作為其完成快感的對象。母親是原初的對象,[22]母親提供一個過渡性空間(transitional space),此過渡性空間可以轉移到其他的過渡性對象,例如洋娃娃、遊戲、寫作、藝術,也就是所有創造性行為都是主體以主控的方式演出他與母親的關係--失去而復得,如同佛洛伊德曾經討論過的fort-da遊戲(拉康也據此討論象徵系統的開始)。克莉絲特娃指出﹐此種重演創傷場景與重新捕捉失去之對象的藝術活動﹐便成為詩人的戀物對象︰在此戀物關係中﹐有個根深蒂固的信念﹐便是其「母親」是具有陽具的(the mother phallic)﹐而自我永遠不會與其「母親」分離﹐沒有任何象徵是足夠強大到可以切斷此依戀關係。在此共生的狀態下﹐詩人只有佔據「母親」的位置﹐從戀物航向自體情慾。藝術便是將母性空間(maternal chora)重新投資於象徵秩序中﹐從而踰越其規範﹐這便是「變異的主體之結構」。(perverse subjective structures.) (Kristeva: 1986, 115)[23] 克莉絲特娃特別指出﹐藝術中「死亡」是指涉過程中的內在疆界﹐是被主體內化的死亡﹐也是踰越中主體必須穿越的疆界 (Kristeva: 1986, 120) 。 巴代耶曾經花過很大的工夫討論我們如何面對暴力與犧牲場景的問題。他認為﹐自殘與犧牲﹐在最基本的層次﹐只是「對於曾經被一人或是一個團體接納內化之物的拒斥」(Bataille: 1993, 70)。同樣的﹐我們面對此犧牲場景所經驗的排斥心理﹐以巴代耶的話來說﹐只是被一陣要嘔吐的衝動所引發的恍惚﹐要嘔吐出另一股巨大的力量,這是威脅著要吞噬我們並且自我毀滅的內在力量(Bataille: 1993, 70)。在《內在經驗》這本書內﹐巴代耶也說明為何這幅酷刑中的中國人的照片如此震撼他﹐既被迷戀又深感排拒:「就像是我要雙眼瞪視著太陽﹐我的眼睛開始反叛。……我被自己要摧毀內在抗拒毀滅之力量所吸引」(Bataille: 1988, 120, 123)。對於毀滅既愛又恨的曖昧態度﹐以及全然放棄自己的狂喜﹐正是巴代耶解釋宗教出神與極度恐怖之間必然關連的神祕基礎。 對於這種面對被扭曲破壞的醜陋肢體﹐既被吸引又強烈排拒的曖昧態度﹐克莉絲特娃在《恐懼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的推離理論(abjection)更能夠說明清楚。克莉絲特娃說﹐藝術家處於推離作用中主體疆界模糊的位置﹐「其內在感受的是受難﹐而外表顯現的則是恐怖」(Kristeva: 1982, 140)。被推離的是身體/文化/歷史所要清除的不潔之物。其所以要被推離清除﹐是因為此異質之物會「威脅到同一性、系統、秩序的建立」。因此﹐所有不尊重疆界、位置、法規的﹐所有曖昧的﹐綜合的﹐居於其中的﹐都要被清除(Kristeva: 1982, 4)。被切割肢解的軀體﹐剜割斷裂的眼球﹐器官﹐內臟﹐頭顱﹐是我們畏懼面對的最極端的「推離物」。藝術家時常卻在暴力、瘋癲、狂喜的場景中﹐透過藝術﹐或是語言﹐以「透工」(working-through)的方式﹐將此「推離物昇華」(Kristeva: 1982, 26)。經歷此推離物的昇華過程﹐或是符號化的過程﹐我們也開始理解我們內在被壓抑或是排除的經驗何在。 有關前衛藝術中的暴力性格,我們可以在《黑色太陽》(Black Sun)中看到克莉絲特娃所繼續發展的理論。克莉絲特娃認為,文學、藝術與宗教都是抗拒意義崩解的努力。在字裡行間隱藏的抑鬱、憎恨﹐便是我們要去揭露的﹐亦即是無意識中的死亡﹐不可再現的死亡。詩人在語言中設立「母親」﹐並且以施虐/自虐的方式對待此母親﹐或是自己。無論是推離﹐或是自殘﹐都含有跨越死亡邊界的動作。「死亡趨力銘刻於形式的解體、扭曲、抽象、挖空與變形之中」(Kristeva: 1989, 26-7)。這就是克莉絲特娃所謂的藝術創作中的「弒母」行為﹕將對象性慾化。這是主體個體化﹐尋求自主﹐也就是主體之形成的必要起點。憂鬱哀傷之主體將母體對象內置(introject)﹐進而執行自殺式的行為﹐以免除弒母的罪惡感。然而﹐主體為了抗拒死亡﹐在文字與藝術中﹐透過想像﹐將「她」以「死亡形象」(image of death)呈現﹐因此﹐the feminine便成為死亡形象﹐以便屏障防護我對閹割的畏懼。「我攻擊她﹐侵犯她﹐再現她﹐以免我為了殺她而自殺﹐以免我陷入憂鬱而無以自拔」(Kristeva: 1989, 28)。 巴代耶與克莉絲特娃對於藝術中的犧牲、自殘、暴力與死亡的說法﹐都可以協助我們理解陳界仁作品中的暴力與死亡的殘暴衝動。但是,要更為深入地理解陳界仁對於創傷身體的迷戀﹐我們還需要回到他的成長脈絡,以便了解為何陳界仁特別會對於醜陋殘損而破敗的軀體﹐有強迫性的迷戀、觀看與再次損毀的慾望?這個陳界仁需要攻擊、侵犯、再現的「母親」軀體,是哪一種原生狀態?牽連了哪一些環境因素?承載了哪一些歷史的創傷環節? 陳界仁成長於一個小眷村﹐在景美溪與新店溪交會的一塊畸零地﹐就在軍事法庭之旁。他從小在此軍事法庭四周玩耍﹐時常好奇此高牆之內關著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眷村在新店溪旁﹐每年夏天在溪邊嬉戲﹐一定會看到幾次從上游漂浮下來的死屍。小孩子們還會找木棍將被草叢困住的浮腫屍體翻轉過來﹐瞧個究竟。陳界仁所住的眷村﹐都是十分低層的士兵﹐隨國民政府的軍隊南征北討﹐輾轉流離﹐戰敗後落戶台灣。由於貧窮,這些老兵所「娶」的妻子﹐多半也都是本省籍貧窮人家的女兒﹐或是孤兒養女﹐或是原住民。每個家庭都有一大群小孩。據陳界仁說﹐或許由於某一些被娶來的妻子就是智障者﹐或是父母年紀過大而繼續生育﹐他從小在這個村子裡就看到許多瘋子或是白癡。他每天都陪著鄰居一個身軀壯碩的智障小孩一起上學﹐而他自己的弟弟也是白癡。他與這個白癡弟弟同住一個房間﹐這個白癡弟弟全身癱瘓﹐無法清理自己的糞便﹐要家人協助處理﹐也因此他長年躺在床上﹐赤身露體﹐直到十多歲時﹐因病過世。 死亡﹐病症﹐對於陳界仁來說﹐似乎是生活中視覺經驗的一部份。但是﹐這些生活中的視覺景象﹐其實卻是與歷史相連的。這種相連﹐並不是以歷史見證的方式聯繫﹐而是透過了隔代而遺忘﹐卻轉移鑲嵌於生活中與身體中的方式相連。 戰亂之後流離失所而落戶台灣的外省族群﹐經歷過驟然失去家園與親人的劇痛;走過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的人﹐也面對過家園變色、親人失蹤死亡的震撼。親身經歷此歷史劇變的受害者之見證、自白或是指控﹐必然會如同Dominick LaCapra所說的﹐有某種特定的防衛性而誇張的症狀式論述(xi)。然而﹐我此處所討論的「誇張的症狀式論述」﹐卻不是歷史災難的受害者所呈現,而來自於他們的後代﹐或謂「後二二八世代」:這個世代在體制性的沈默或是父母對歷史的迴避中成長﹐無法理解此歷史﹐卻承受此災難在其父母親身上造成的真實傷害的效果﹐或是「症狀」。父/母親的威權、偏執、或是轉移的恐懼、失語、精神分裂﹐都可能是此症狀的展現;村落中高比例的瘋子與白癡人口﹐年齡相距二、三十歲的夫妻﹐無法溝通的權威嚴厲卻沈默的父親﹐也會是症狀的一種。 戰後成長的這一代﹐處於戒嚴與冷戰時期所提供的安定和平與知識隔絕狀態﹐就如同被放置於一種被矇住臉面而被剝奪受傷卻不自知的狀態。成長中﹐政局變遷﹐遽然面對歷史認知被肢解的體認﹐以及面對認同體制被閹割的事實﹐則如同經歷一場認知創傷。 在訪問時,陳界仁曾說,八○年代中期,他還參加了幾次街頭劇場,進行年輕時的他對體制的控訴與抗拒。[24] 然而,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五年,他陷入一種無法創作的狀態。根據另外一則相當逼近實情的訪問報導所言︰「陳幾乎處於半獨居的生活。常常一天說的話只有「老闆,給我一包白長。」不工作、不創作,不動,……那麼陳界仁在作什麼?「幻想。我常常一個恍惚,一天就過去了。這段時間中有一年,幾乎徹底的什麼事都沒作,有一天忽然發現,啊,過了一年」(鄭雅文)。的確,陳界仁這個時期無法創作,但是,他的幻想卻時時出現日後創作的意象。陳界仁說︰「這個年代,一切趨於同一,我們越來越難找到彼此的差異,只有夢。」(鄭雅文)。因此,在夢中,在幻想與恍惚中,他的幻想製造了強而有力的意象,呈現他的差異性的意象,並且以電腦光筆捕捉了他幻想中的圖像。 陳界仁曾經說﹐處理這些影像﹐就像是亡者進入陰間﹐經過「孽鏡」﹐在鏡前看到一系列自己前世的靈魂。他在所有刑罰受難者身上﹐看到與自己相連的影像。林志明便提出他對於陳界仁所說的「孽鏡」內涵的「監視」功能的看法︰「在中國,鏡子從來不只是一種反射的工具,它一直是一種觀察的工具(古人以鏡為鑑的『鑑』字中即嵌有『監』字)。監視是恆常存在的,而且絲毫不漏,……孽鏡上出現的影像不一定只是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因為觀看本身就可以是一種『懲罰』」(林志明 68)。這種傅柯式的詮釋,自然是很根本的存在於陳界仁的圖像構成中。 但是,我認為﹐陳界仁真正處理的﹐並不是監視系統,或是歷史事實與「外在現實」,而是鑲嵌了歷史與他自己個人處境的創傷經驗,他的「精神現實」(psychic reality),或是克莉絲特娃所說的承載精神銘刻(psychic inscription)的「真實」(the real)。在《精神分析辭彙》(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中「精神現實」這一條目中,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J. Laplanche & J.-B.Pontalis)指出,佛洛伊德曾經說明無意識過程不僅毫不考量外在現實,並以一種精神現實取而代之。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說明,此「精神現實」便是指無意識慾望與其相關幻想(Laplanche & Pontalis, 422)。在「原初幻想」這一條目的討論中,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也對此「精神現實」做了詳細的解釋,並且指出這種「後遺的」(deferred)與「回溯的」(retrospective)的幻想,將「現實主義」的原初場景轉向「精神現實」的原初幻想(Laplanche & Pontalis, 168)。這種精神現實,與克莉絲特娃所說的「真實」較為接近:克莉絲特娃所說的「真實」,便是符號界的衝動,或是無意識的欲力,類近於拉康所說的「真實」the real與「想像」the imaginary。然而,克莉絲特娃強調,拉康堅持「真實」的空無(void),而她認為其中更為重要的是自戀結構,已經含有精神的刻印痕跡(psychic inscription),比空無有更多的東西 (Kristeva: 1996, 23) 。或者,我會認為,此「真實」是鑲嵌了歷史的刻印。 因此,若我們要回答「透過電腦的光筆繪圖,陳界仁捕捉到了什麼」的問題,我們就必須透過精神分析式的閱讀與理解,回溯他的精神現實與銘刻物:陳界仁說﹐成長於戒嚴時期﹐如同被「關在」監獄的外面﹐什麼都看不到也聽不到。我們會注意到,就是這種要觀看與聆聽原初場景的慾望﹐要回到創傷原點的衝動,使得他不斷透過幻想圖像回到歷史創傷的場景﹐處理各種歷史斷裂的暴力時刻。他所捕捉到的,是他看不到,卻鑲嵌在身體之內的意像。透過一連串過度而誇張的淨化與犧牲儀式,透過破壞自己的「身體」,陳界仁將自幼經歷到的面對死亡的「鈍感」尖銳化﹐並且極力將自己與弟弟難以區分的身體反覆公開的切割;這種過程,也將他面對歷史的「鈍感」尖銳化。因此﹐這些最為暴力與醜陋的方式﹐是他的「孽鏡」,是他的精神分析過程,使他生命中的各個歷史與個人的創傷場景得以反覆出現。 如此﹐或許我們便可以解釋如陳界仁式的自殘暴力所面對的﹐是如「母體」一般的屬於台灣的歷史記憶與生存環境。此特殊處境﹐便以最為極端激烈的中國現代化建國霸權與排除機制﹐反覆展現於他的圖像之中。陳界仁凝視刑罰的圖像﹐凝視暴力執行之後的傷口﹐反覆讓自己重新經歷此傷殘的過程﹐讓自己面對自己對於暴力殘酷的排斥﹐以及此驚悚場景所帶來的恐懼與完全放棄自我的狂喜﹐就是一種以身體驗證此歷史創傷的症狀演出──重新訪視屬於台灣/中國的創傷史。 在訪談錄中,克莉絲特娃與Catherine Francblin討論她的《靈魂的新痼疾》( New Maladies of the Soul)時指出,許多藝術家並不了解他們所創作出來的圖像意義。如果我們閱讀我們時代的圖像,消費之後,卻不試圖理解這些圖像的意義,我們便無法面對其背後的問題。克莉絲特娃認為,拉康指出語言背後象徵系統的問題,卻忽略了背後的趨力,因此,她建議我們必須面對語言背後想像建構的面向 (Kristeva: 1996, 87)。這也就是為什麼陳界仁指出他的圖像系列的批判計畫,但是,有更多的意義,卻需要我們進行精神分析式的探索,捕捉其中的想像層面。於是,我們在陳界仁所製作的這些類似「受難」與「聖像圖」中,看到了如同羅逖(Richard Rorty)所說,一個強悍的詩人(strong poet)製造出了新的語彙,這個「詩」的語彙深刻地「說出了」(enunciate)他的差異處境,也說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存在問題。[25] 閱讀陳界仁,就如同閱讀一個強悍詩人所製作的翻轉概念的新的視覺語彙:我們在深刻的個別性差異處境中,才看到了屬於此時代的底層問題。 面對台灣當代藝術家如陳界仁者所持續創作的非寫實而具有災難性質的視覺圖像﹐我們除了看到了他以圖像思維所進行的「現代化」歷史詮釋與批判﹐看到了此圖像以症狀演出的方式揭露屬於台灣的特殊歷史經驗以及複雜心態結構﹐其實在閱讀與對話的過程中,我們同時更經歷了自身歷史經驗的回溯與喚醒。我在處理陳界仁作品圖像的過程中﹐不斷翻閱相關的資料與圖片檔案﹐例如王永寬的《中國古代酷刑》、陳綬祥編的《舊夢重驚︰清代明信片選集》、陳申等人編著的《中國攝影史:1840-1937》、徐宗懋編的《中國人的悲歡離合(1935-1949)》、錦繡出版社發行的《二十世紀中國全記錄》﹐一再反覆被其中的中國與台灣的歷史圖像強烈地震撼。我因此了解﹐陳界仁的圖像中特殊的歷史經驗與心態結構是屬於陳界仁的﹐也是屬於我們的。 這些視覺經驗﹐如同陳界仁幼年在軍事法庭的高牆外所試圖觀看的﹐是在看不到之處而看到的圖景。而這些觀看﹐也如同對於原初創傷場景的探究﹐是對於經過戒嚴與冷戰時期而被切割的歷史以及被壓抑排除之記憶的索取。症狀的反覆演出中﹐「真實」從這些圖景中的傷口裂縫處向我們逼視。因此﹐James Elkins所說「我們知道不能夠或是不應該看到的景象」﹐這個「真實」﹐不只是死亡的景象或是歷史的體制化排除與殘暴﹐而更是我們以身體來承受的歷史肢解與認知斷裂,以及我們因此而參與並且曾經執行過的排除暴力以及淨化工程的隱藏記憶。只不過﹐我們的暴力與淨化是被隱藏在「正常化」的表象之下﹐以各種瑣碎的方式執行﹐例如某一種立場的選擇﹐某一種歷史的敘述方式等等。何時﹐被我們排除的歷史記憶會得以浮現?何時﹐我們能夠與被我們排除的經驗取得和解﹖又或者﹐若我們持續不願意回顧﹐而這個暴力與淨化的企圖會在我們不自知的狀況下再度尋得管道而取得立即疏通與實踐的途徑呢? *此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NSC89-2411-H-030-008之部份成果。英文論文“The Gaze of Revolt: Chen Chieh-Jen’s historical images and his aesthetic of horror” 曾經於華沙「變遷社會文化困境」國際研討會(Cultural Dilemmas Druing Transitions, 15-17 OCTOBER 2000)發表。經大幅度修改擴展,曾於清大社會所提出,與該所同仁討論,並於第25屆中華民國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發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01年5月19日∼20日)。此處論文為再度修訂的版本。此期間,張小虹、廖朝陽、陳光興、宋文里先後提出回應意見,對此文之發展助益甚大,特在此致謝!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