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側記 離散語碼:媒體筆作為點狀書寫主體
2022-06-17
在論文跟影像之間,「論文電影」橫切開其交匯之處。在圖像與聲音之間,「媒體筆」提出 將它們當成一套整體的批判語言。
在亞洲轉型媒體實驗室系列演講的最後第二講,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的林欣怡副教授在今日以《離散語碼:媒體筆仍為點狀書寫主體》為題跟我們分享。她用夾敍夾議的方式,引用着影像作品,兼顧影像和文字的探討,把我們帶到當代媒體和影像實踐的技術和思考裡面。
林教授首先對比電影和文字書寫、電影語言跟文字語言的差異。在早年的電影討論裡,影像和文字看似是割裂的。譬如在早期的法國電影導演馬歇巴紐(Marcel Pagnol)看來,電影的影像是次要的,寫下故事的劇作家或小說家的文字才是主要的。何內.克萊爾(René Clair)則回應巴紐:每個調度場面的人都是作者。
法國學者梅茲(Christian Metz)進一步拓展這種電影知識論的討論:他用「電影語言」 來理解電影獨特的語言系統,在電影的世界,不存在影像/文字的二元框架。電影呈現給我們知覺的是一整套語言。
林教授再把這種電影語言的討論推展到田野研究的領域。電影語言是對感官經驗的轉譯。人類學家的民族誌書寫更加是一種文化轉譯。在這個意義上,學術研究者相手持的「筆」也跟電影拍攝人的「媒體筆」(media stylo)連結上了。
螢幕紀錄片(screen documentary)與錄像論文(video essay)這些概念,其實表現為當代新媒體環境下的「論文電影」(Essay film) 格式。林教授繼續拓展我們對論文(essay)的理解,引用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說法,「essay」不只是一種書寫文體,更是一種關於「實驗行動」(the act of essaying)多種樣態的書寫形式。
愈來愈多媒體研究者已陸續投入了這場論文電影的實驗大潮。在林教授播放的電影片段裡,我們不但看到研究者-製作人用電影來思考和發問。在諸多看似片段式的錄像論文裡,我們也見到他們用他人的影像來剪接再製,上傳到免費平台,用自己的電影語言跟他人的電影語言對話,用影像來形成自己的觀點(又或者呈現為開放性的多重觀點)。
像法國新浪潮導演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所說的「攝影機筆」論,電影也是一種語言,可以不只是跟從敍事邏輯,而是讓電影作者通過影像在膠卷上寫下他的哲學。錄像論文導演費登(Eric S. Faden)就跟隨阿斯楚克的說法,提出「媒體筆」(media stylo)作為媒體批判的創作方向。電影作者能夠用影像去批判,以至於批判性的揭露影像本身。
在愈趨分眾、支離破碎而又無比龐大的當代媒體世界,「媒體筆」的運用空間愈來愈多,也愈來愈靈活。人人都能生產影像,人人都能評價影像。圖像縮放、慢速、重播以至於「超級剪接」(supercut)等的編輯技術為人所廣泛使用。巨量的影像數據庫提供無數材料給影像作者,也使得影像作者的文本以滑動、蒙太奇、多點並置的形式表現出來。
電影文本慢慢由過去「不可觸及」的文本,在這些當代技術下「可觸及」的文本。數位媒體的「蒙太奇語言」 既保留原來的不透明性,又打開了無數詮釋和理解的空間。作者具像地通過影像發問,觀者亦被邀請參與在電影當中。這些電影文本愈趨的抵抗單一的詮釋,要求觀者承擔更多責任去建構其意義。新媒體紀錄片導演如庫佛(Red Coover)等就把民族誌與人類學者的方法論放在他的紀錄片裡。藝術家赫希豪恩(Thomas Hirschhorn)就在他的作品裡表現影像化的戰爭暴力,是絕對的不可還原和不可再見證。在這些層面的討論裡,(文化)翻譯是絕對不可翻譯的,而又是絕對可以把不同語境連接起來的(帶着絕對不可翻譯的前設去靠近和互相理解)。
這種方法表現為離散語碼(discrete coding),又具有其獨特的當代潛力。在新媒體所形塑的世界裡,我們的生活亦深嵌在數據和感知的離散分佈當中。而我們去回應、去體現、去質問這種當代處境的方法,也愈發的落在離散語碼的影像實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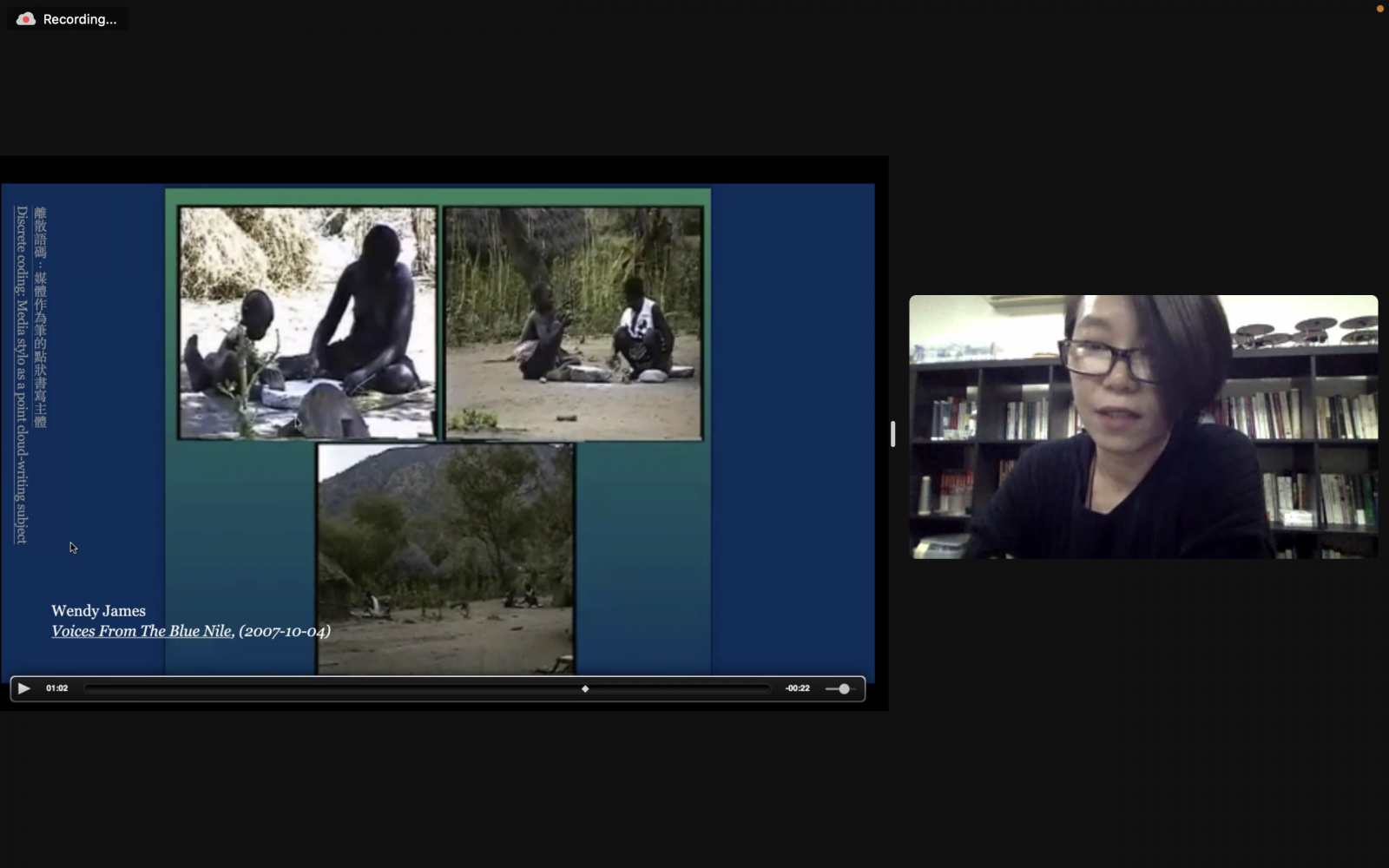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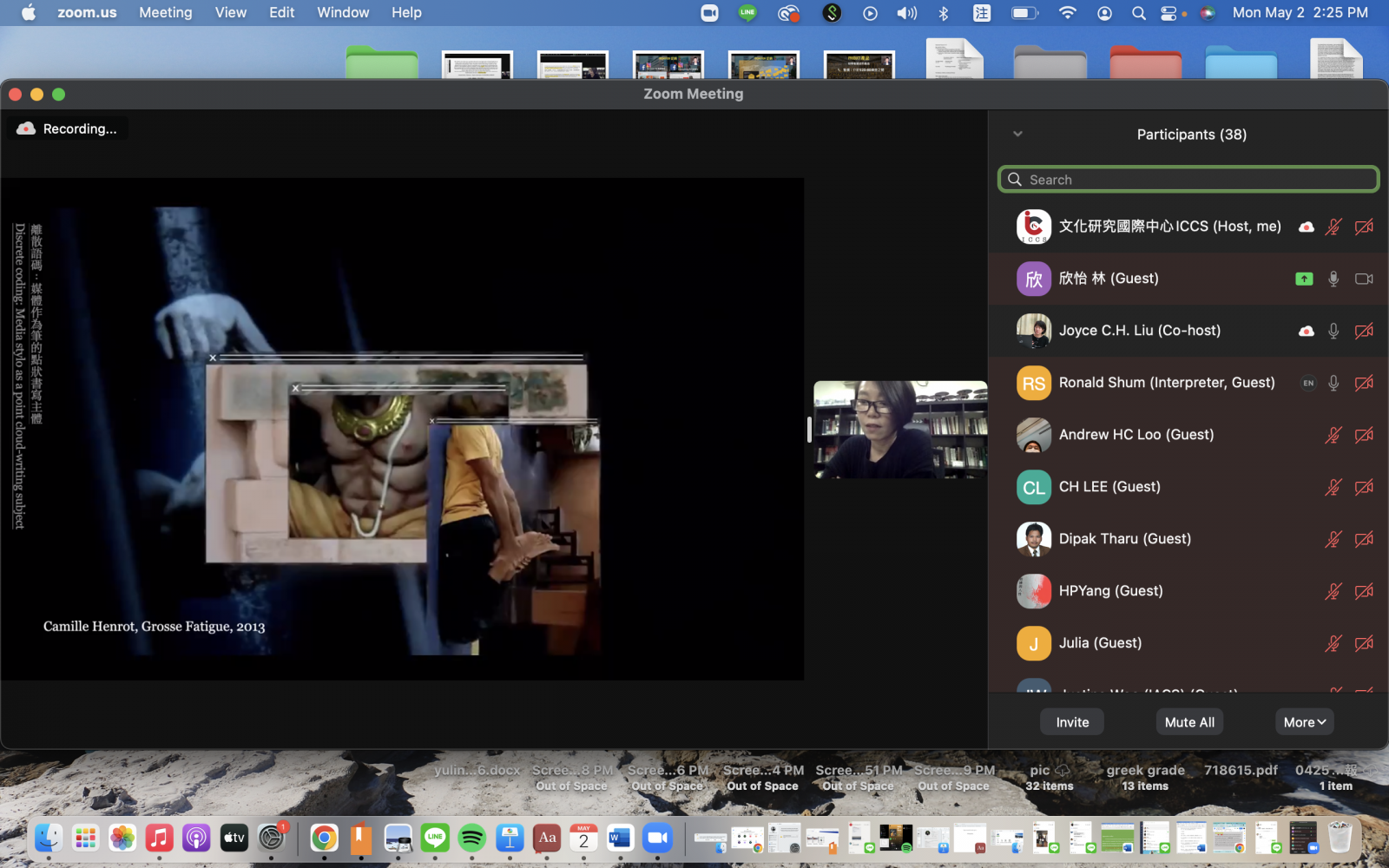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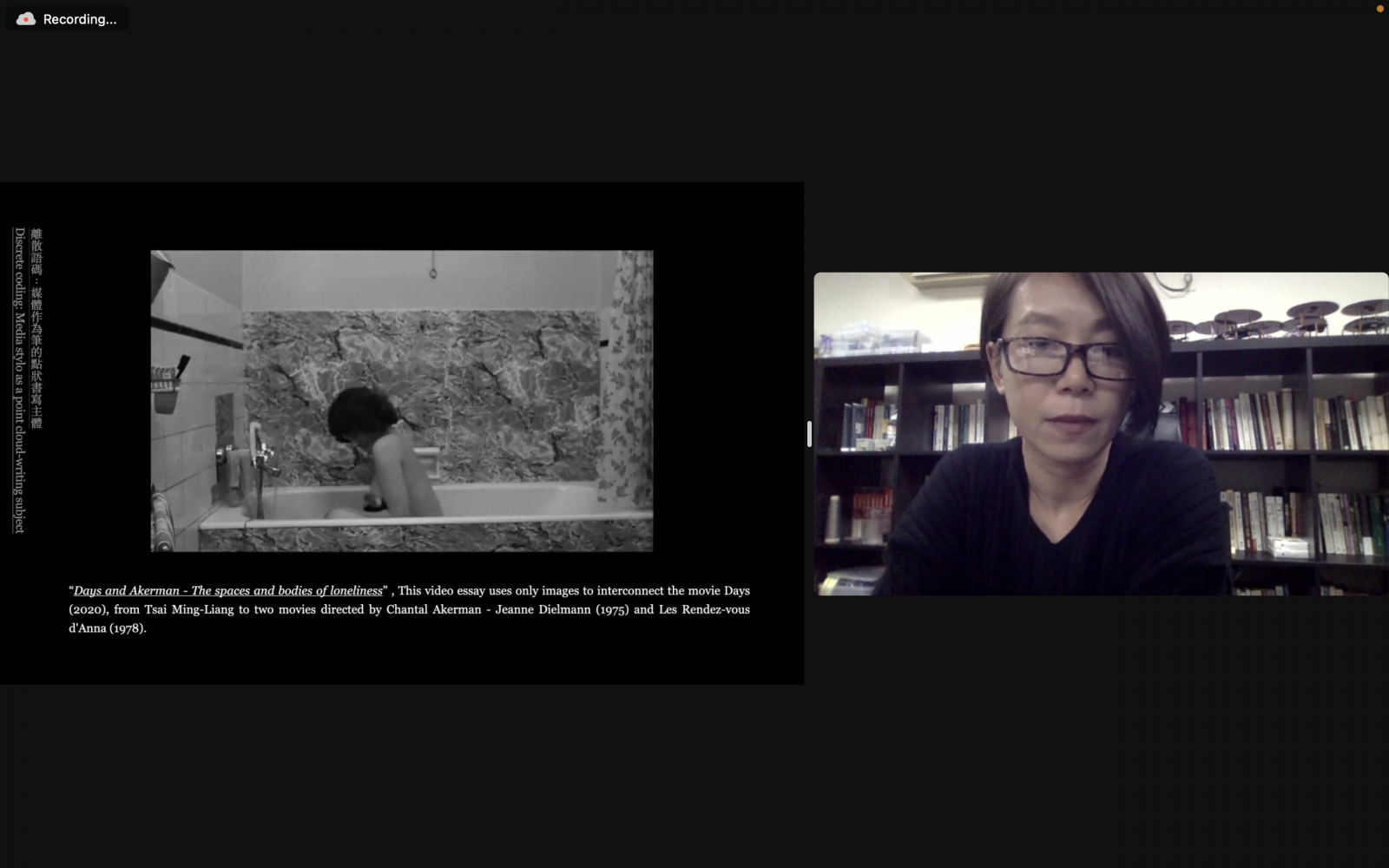
近期新聞 Recent News


